 |
相關閱讀 |
李昕:我帮钱锺书打《围城》官司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1993年6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实施两周年之际,北京各大报刊忽然之间接二连三地刊登了这样的热点新闻:“《围城》再度被围”,“《围城》被盗印本围困,钱锺书欲依法突围”,“《<围城>汇校本》版权烽烟起”,“钱钟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陷入侵权困扰”,一时间,一场有关《围城》的版权官司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这些新闻,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5月27日邀集各大媒体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而在发布会上,代表出版社发布新闻的人就是我。 (一)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下简称人文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1992年初冬的一天,社长陈早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递给我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一看,书名是《围城》,心中不免诧异。《围城》在人文社印行十几年,使用的一直是灰底黑字的封面,我不记得换过呀。陈社长告诉我,这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川文社)的《<围城>汇校本》,现在正在大量发行。 《围城》汇校本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署名钱锺书着,胥智芬汇校。我没有听说过胥智芬其人。再看内容,不过是将《围城》1947年在《文艺复兴》杂志发表的版本,1948年在晨光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和八十年代人文社出版的定本进行了比对,把不同版本的不同用词用字一一标示出来,作为注释,注在每一页的下方。整体上看,书的内容就是一本加入了若干注释的长篇小说《围城》,但注释的内容,一概只是关于某个字词在其他版本用作其他字词一类的信息。其中除了作者在定本中改正过来的个别错讹,也有经编辑更正的解放前旧版中的排版错误,更为大量的是由于汉字简化而出现的同一汉字的不同字体(例如旧版作“一枝笔”,新版作“一支笔”;旧版作“拿着”,新版作“拿着”等等),这些都被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来,全书号称两千多条注释,大量属于最后这种情况。看了不禁令人发笑,以为这样的“汇校”,实在太不专业了。一看便知,所谓“汇校”不过是障眼法,川文社真正想出版的是长篇小说《围城》。 谁都知道《围城》现在是热门书。1990年《围城》电视剧上映之后,人文社的长篇小说《围城》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不法书商乘机盗版,国内几年中先后出现了近20种盗印本,总印数据估计逾200万册。但凡盗版,都是偷偷摸摸地印,悄无声息地卖,让你查不到,抓不着。但是川文社的《<围城>汇校本》,却是打着“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版本”旗号,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公开销售,他们的大言不惭和理直气壮着实令我震惊。 陈社长向我介绍说,这本书是1991年5月出版的,6月份,钱锺书先生收到四川方面寄来的样书,当即和我社编辑联系,表示不知此事,问出版社是否同意如此“汇校”?得知此书是四川方面擅自出版之后,钱先生即委托我社与四川方面交涉。7月23日,我社代表钱先生致函四川省新闻出版局,要求查处川文社出版《围城>(汇校本)侵害钱锺书着作权和我社专有出版权的行为。8月8日,川文社曾经回函,承认了自己的侵权行为,表示愿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承诺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陈社长见信后曾表示:“都是兄弟社,好商量。” 但是,陈社长说,“没想到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在1991年8月以后,川文社又继续重印发行这本书,到现在总数累计超过10万册。而且,他们甚至把封面上的“汇校本”三个字也取消了,侵权更加明目张胆,变本加厉。 “他们这样搞法”,陈社长说,“是要逼着我们打官司呀。” 深入一想,我明白了。这个官司不能不打,而且只能打赢,不能打输。因为如果输了,那么人文社多年积累的大批现代文学名着,都可以被别人轻易拿走,巧立名目,另行出版,这样《着作权法》所保证的专有出版权就名存实亡了。所以这个官司并不仅仅为了这一本书,而更重要的是要在《着作权法》实施以后为出版界立一个规矩,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陈社长告诉我,现在钱锺书先生已经全权委托我们出版社代表他打官司。我们替钱先生委托了两位律师,但是社里也要有一个代表负责此事。他看了看我说:“你是我的助理,你办事,我放心。” 这样重要的任务,我当然要接下来。但是我知道打官司需要出差,而我的家庭有些具体困难。因为家住得很远,我每天上下班都得接送孩子,不便出差。如果能够有一套位于出版社附近的家属宿舍,孩子放学可以自己回家,这问题就解决了。虽然当时我作为社长助理,在等待分房的人中排名第一,但是出版社下一批分房子,大约至少还要等半年到一年。 陈社长说,“那我就提前给你分一套房子。”此言一出,我知道他是下定打官司的决心了。 (二) 接受任务之后,我和社里主管版权事务的副总编李文兵、总编室主任冯伟民、版权室负责人王睿以及社里为此案聘请的两位律师陆智敏、李浩一起开过几次会,大家统一认识,研究对策。 陆律师情绪激动,显然是窝了一肚子气。他不久前刚从成都回来。因为川文社早先曾表示愿意“抱着诚恳态度妥善解决这一纠纷”,他去成都找川文社社长研究解决方案。谁知那社长“工作太忙”,竟然让他在宾馆里“待见”了9天。最终见面,那社长的态度陡变,矢口否认川文社有任何侵权行为,连陆律师代表钱锺书查询此书印数也遭到拒绝。 “他们现在全不认账了”,陆律师说,“而且好像有恃无恐,并不怕我们打官司。”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和钱锺书先生一起打官司,钱先生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从陆律师那里,看到了钱先生有关此案的一系列信函,并了解到他对此案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钱先生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支持。 1991年6月钱先生收到《<围城>汇校本》样书,扉页上,川文社一位编辑给钱锺书、杨绦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样说:“去年,顿生念将钱老《围城》弄出汇校本,曾托人函示钱老。现书已出,乞支持这项吃力不讨好的造福子孙后代的做工。”钱先生立即致函人文社编辑黄伊,指出此书是“一种变了花样的盗版”,说:“托人函示云云,全无其事,语意暧昧,想蒙混过关;假如有此事,得我同意,何必‘现’请‘乞支持’?《出版法》(按,指《着作权法》)公布后,想此人感到紧张,故作此补笔,向我当面撒谎。……特此奉告,随贵社处理吧。”然后便向人文社开具了全权委托书。 人文社同川文社展开交涉以后,曾询问他们的编辑所言“托人函示”是否确有其事。对方答复说,“曾委托‘钱学系列丛书’作者之一的陈子谦同志”“书面或口头报告钱锺书先生”。钱先生闻知后,立即向陈子谦查询。陈回函,称此说“纯属捏造”,他们这样说,“也损害了我的名誉”。“这个社的一些人对《着作权法》一点也不尊重,这是我不能容忍的”。钱先生接此信函,更加证实了自己最初的判断。 对于“汇校”本身,钱锺书和杨绦先生也都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围城》责任编辑黄伊前往府上拜访钱杨二老时,谈论起“汇校”问题,杨先生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些书,因为年代久远,有人研究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围城》这本书,作者和我们都还活着,有什么必要搞‘汇校本’呢?”钱先生则非常气愤地表示:“什么‘汇校本’呀,这是变相盗版嘛。要使用我的作品,也不预先征求我的意见。再说,个别排版错误,或者疏漏之处,我在再版时已经改了过来,作者有对他自己的作品的修改权呀,有什么必要特别将它标明出来呢?” 基于钱杨二老的认识,后来我和陆律师等曾四出拜访文艺界和法学界、版权理论界知名人士,征询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汇校”的意见。我们最初估计到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敢奢望得到所有专家学者的支持。然而无论大家在一般意义上如何评价“汇校”的价值,一旦联系到《<围城>汇校本》的个案,几乎所有专家都无一例外地指出,川文社已对人文社构成侵权。特别是巴金老人来信,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居然有人要出《家》的‘汇校本’,这是否定版权时代的做法,我不会同意的。” 这些专家意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于是,我们在1993年初,给新闻出版署几位主要领导致函,寻求支持。函中表明了我们对“汇校本”的看法: “众所周知,‘汇校’是我国古籍整理的一项专门工作,对于年代久远、原作散失、并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古籍,进行版本汇校,判别文字真伪,是有意义的工作。古籍版本没有专有出版权的问题,因而翻印使用流行版本不构成侵权。但当代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修订定稿,不存在判别文字真伪的问题,而当代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出版权享有者及作者同意,任何翻印原作都是侵犯着作权及专有出版权。” 为此我们指出,如果不妥善处理版权问题,“就把对待古籍的态度和方法套用在当代作家作品之上,是一种常识性错误,而这种错误,必然导致‘专有出版权’的灭亡。” 因为这封信函代表着人文社和钱先生的共同立场,所以我们预先呈送钱先生审阅。钱老阅后,当即复函,写道: “公函理充词正,以老朽外行看来,无懈可击。此非为争几张钞票,乃维持法律之严,道德之正也!” 钱先生“不为钞票”打官司的立场是明确的。在此之前,他已经不止一次严词拒绝和川文社私下和解。 在双方对簿公堂之前,川文社自然明白钱先生与人文社联手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他们曾试图单方面和钱先生和解,以釜底抽薪。1991年8月13日,钱先生在给人文社的一封函件中说:“顷得XX同志电话,告我云:四川文艺出版社派人来京,一面请XXX同志向贵社疏通,一面请XX同志向我疏通,要求‘送钱’给我‘私了’。我向XX说明此事已交贵社办理,秉公执法,我不和他们‘私人’接触。特此奉闻。想贵社必能维护《出版法》(按,指《着作权法》)之尊严也。”9月30日,钱先生再次来函,表示“不与对方‘私相授受’”,“决不背前言,‘私了’一节请放心。” 川文社也很有一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当面送钱不成,又改为汇款。当年12月中旬,钱先生莫名其妙地收到某工商银行的领款通知,告知9800余元的汇款已到。钱先生猜想,准是川文社所为,请人去银行查询,果然不错,当即表示拒收,此举引来银行工作人员一片诧异。 钱先生的态度可谓绝决。我想,他这是在力主依法办事的同时,也在力挺人文社。当然,之所以力挺,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出版秩序,为了游戏规则的公平和公正。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我们帮钱先生打官司,还不如说是他老人家在帮我们打一场维权的官司呀。 (三) 说到这里,读者大概会问:川文社开始曾经认错,为什么后来改变态度,公然继续侵权,且有恃无恐? 这是因为他们拿到了“尚方宝剑”。 川文社是不肯轻易认输的。两年来,他们也一直在为自己的侵权行为寻找“合法”的理论依据。他们托人找到国家版权局,就“汇校本”问题寻求法律援助,结果便如愿收到了1992年11月13日该局办公室的标明(92)权办字第37号信函。该函对《<围城>汇校本》发表了几点意见: “一,‘汇校’是对原作品演绎的一种形式,汇校者依法汇校他人作品,对其汇校本享有着作权。 “二,胥智芬未经钱锺书的许可对《围城》进行‘汇校’侵犯了钱锺书的着作权(使用权和获酬权)。四川文艺出版社在未作任何调查和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出版侵权作品《<围城>汇校本》,应承担连带责任。 “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与钱锺书签订的合同有效期间对《围城》一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根据《着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汇校’不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畴,钱锺书又未将‘汇校’这种使用形式转让或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使用,因此,胥智芬及四川文艺出版社未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一书的专有出版权。” 这可以算是一份版权事务的“裁定书”。但如此违背常识的裁定,几乎可以用“荒谬”二字形容。它的副本寄到人文社,令我们大感诧异。国家版权局是《着作权法》的权威解释机构,然而他们竟然可以随意地把作者对作品的着作权转移给“汇校者”所有,而且还把一家出版社有计划、有组织的侵权行为(这是川文社已经承认的),解释为一个不明身份的“汇校者”的个人过失,仅让出版社承担“连带责任”。如此的一番解释,向钱锺书先生交代,怎么能说得过去?难怪钱先生看了“裁定书”,连称“可叹,可叹!” “裁定书”说到“汇校本”的出版并不侵犯专有出版权,我们觉得事情重大,需要和版权局协商对话。 在一场安排好的对话会上,双方各执一说。版权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始终揪住一条:《着作权法实施条例》关于专有出版权的规定,只讲包括“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并没有把“汇校本”包括进去。所以,如果认为“汇校本”也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但我们强调指出,“汇校本”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不就是“原版”和“修订版”吗?小说还是这部小说,作品还是原来的作品,《围城》还是那个《围城》。这个“汇校本”不过是以“汇校”的名义翻印“原版”和“修订版”。 我们引用钱先生致人文社信函中的话作为依据: “《围城》原印本虽非由贵社出版,但《围城》作为作品,已由作者正式同意贵社出版,权属贵社。原本上改动处皆属作者着作权,现既已由贵社出版,则翻印原本显系侵犯贵社之违法行为。” 人民文学版《围城》 但版权局办公室一位处长对钱先生的话报以轻蔑,他冲口而出:“钱锺书不懂法!”我们见到这一情景,便知道协商对话不可能奏效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官司,通过法律程序,把国家版权局的“裁定”搬倒。但谁都知道,这是极为困难的。国家版权局是国家的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着《着作权法》的解释权,他们的言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律。他们支持川文社,给我们形成的压力很大。 四川方面已经放出风来,说是“诚惶诚恐地等待”与我们“对簿公堂”。这种以退为进的口气,似乎是胸有成竹。 而钱锺书先生明确表示,官司要打,但他不能自己出面了。这一阶段,钱先生身体状况不佳,与我们沟通,大多通过女儿钱瑗。钱瑗因为小时候随钱杨二老在清华园生活,住处离我父母的家不远,她熟识我的父母和大姐,也知道钱杨二老在清华外文系任教时曾与我父亲同事。所以她得知人文社派我帮助钱先生打《围城》官司以后,便回家把这消息告诉二老,二老自然非常高兴。钱瑗很感慨地对我说,父母年事已高,很多事都需要有人帮忙了。如果人文社不能利用法律手段了结此事,那她父亲岂不是“任人宰割”了吗?这话说得令人动容。 在我们这里,此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没有退路。专有出版权是我们面前的一道大堤。洪水袭来,只有保卫大堤才是求生之路。否则堤坝决口,人人遭殃。 (四) 为了给钱先生,也为了给自己的出版社讨回公道,我们于1993年底,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胥智芬和川文社。 为什么要在上海立案?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川文社在四川的势力和影响,担心地方保护主义因素、人情因素干扰司法公正。由于我们了解到胥智芬在上海任职,所以便理所当然地把上海选择为侵权发生地。这一下,使得严阵以待的川文社似乎有些措手不及。 但川文社迅速摆出应战的姿态,他们立即在上海聘请了着名律师朱某作为委托代理人。朱律师有一张"名嘴",曾经打过许多着名的官司,也算是律师界的知识产权问题专家。 我们这边,则在抓紧时间补充证据,我们邀请了多位权威法律专家表态,请他们写下自己的专业意见,准备提供给法庭。同时也动用媒体制造舆论,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外,我也亲自执笔写了一篇长长的新闻通讯,题为《<围城>(汇校本)盗版风波》,刊登在人民日报主办的《大地》杂志上。 几个月后,这场官司在上海开庭。我和两位律师一起去参加法庭辩论。那天的辩论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天。双方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对方聘请的朱律师不愧辩论高手,他非常善于钻空子,找漏洞,发言时始终保持洪亮的嗓音,自信的语气,时时发出咄咄逼人的提问。但因为我方提出的证据严谨、全面,无懈可击,甚至是无可辩驳,所以朱律师虽巧舌如簧,也难以提供言之成理的见解,最终无法挽回颓势。 例如,辩论中谈到钱先生拒收川文社的稿费。因为这笔稿费在银行几经周折,最后退回川文社的时间,相对稿费寄来的时间晚了4个月。朱律师以为有隙可乘,不由分说,便认定钱先生在这四个月里的“沉默”,实际是“默认”了这笔汇款,由此也便“默认”了“汇校”的行为,使得“汇校”的性质由“非法”转变为“合法”。至少川文社在这4个月里不构成侵权。这种强词夺理的辩词,谁都知道不能成立。 再比如,细心的朱律师发现,关于《围城》一书,钱先生在1980年和人文社签订过10年期的出版合同,然后又在1992年3月和人文社再次签订10年期的出版合同,两者中间,有一个1年零3个月的空挡期(即1991年1月至1992年3月)。而川文社的《<围城>汇校本》正是在这个空挡期内出版的(1991年5月),所以他说,川文社并没有侵犯人文社的专有出版权,因为那时人文社本身并不享有这种权力。但是,我们出具了钱先生于1991年2月4日给人文社开出的出版授权书,并说明,这个“空档期”未签协议,是因为《着作权法》正待公布,双方约定先以授权方式继续合作,待《着作权法》实施后再根据新的法律规定签订新的合同。这样便一下堵住了朱律师的嘴,令他无话可说。 辩论中我方强调川文社是巧立名目翻印《围城》,“汇校”只不过是个幌子,举出的例证是他们在后来大批加印此书时,竟然将“汇校本”三字从封面上取消,而直接以《围城》作为书名进行征订,此举暴露了他们追逐利润的真正目的。朱律师对此辩护说,这是印刷部门和经营部门的疏忽,并非川文社的故意。他似乎是认为除了编辑部门以外,其他部门都不能代表出版社,如此解释,怎能服人? 在开庭过程中我方律师明显占了上风。休庭后,审判员将双方人员找到一起,例行公事,做庭外调解。但双方都拒绝和解,愿听候宣判。这时双方又短兵相接,辩论起来,核心问题还是“汇校本”的出版是否侵犯专有出版权。朱律师声称“汇校”是一种新的演绎作品形式,可以独立享有版权。这时我接过话茬说:如果这样“汇校”就可以形成新的版权,那么你可以给一本小说后面附几篇评论,称之为“评论本”;我可以给一本小说加几条考证,称之为“考证本”;他还可以给一本小说加几条注释,称之为“注释本”,然后大家都大模大样地翻印使用原作品,各自拥有新的版权。如此一来,这个世界上还能存在保留专有出版权的小说作品吗? 朱律师对我的说法显然缺乏思想准备。他没有说话。散场以后,他走到我旁边说:李先生口才这么好,为什么法庭辩论时不讲话?我笑笑说,我们的律师口才比我更好呀! 这场官司一直持续了三年。经过上海中院初审,上海高院二审,至1996年12月结案。我们没有悬念地获得完胜。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而非《着作权法》)做出判定,除了胥智芬和川文社需要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向钱锺书先生和人文社就侵犯着作权和专有出版权的行为赔礼道歉之外,还需要赔偿钱先生约8万8千元,赔偿人文社约11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这个结果让钱先生和我们长舒一口气,深感我们的法律还是公正的,它终究会与社会良知站在一起。侵权者的责任注定要被追究,哪怕他们有口吐莲花的律师坐镇,手握"尚方宝剑";哪怕他们有权威机构做靠山,而那权威机构号称自己代表法律,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钱先生早就表示“此非为争几张钞票”,他和杨绦先生商定,要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得到赔偿金后,他们将这笔钱和自己着作多年积累的版税一并捐了出去。 (五) 一转眼,这桩历史旧案已经过去了20年,在我的记忆中,它原本已被淡忘。然而不久之前,我在网上无意之中发现一篇文章,题为《〈围城〉(汇校本)十年祭》,作者是当年川文社策划此书的编辑龚某,他在向读者痛陈自己的委屈和苦衷,竟然也引发了我的颇多感慨。 我其实早闻龚先生大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知名学者。从他曾着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可知他有心致力于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他曾谈到过自己希望出版一系列现代文学作品“汇校本”的设想。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围城>汇校本》被判决“死了死了的”之后,“已经酝酿成熟”的一切都“胎死腹中”。 这场《围城》侵权案的法律判决,成了中国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一个着名判例。前车之鉴,足以使效仿者引以为戒。从那以后,人们的确再未见到其他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因为“汇校”而被侵权。我们当初设想,要在《着作权法》实施以后,为保护专有出版权“建立一个游戏规则”,这个目的似乎是达到了。 但是,现代文学作品可不可以“汇校”,需不需要“汇校”?不仅川文社的龚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他在学术界也获得一些舆论支持。例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先生写了《为新文学校勘工作说几句话》,他以郭沫若《女神》的修改和巴金的序跋为例,指出新文学研究者,常常是从一部作品的初刊文、初版本出发,也就是首先要做汇校工作,才开展研究的。因而他认为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本”是为适应这种高层次的研究而出版的,“汇校本”包含了汇校者的严肃劳动,对于新文学研究的工作大有益处。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先生甚至认为《<围城>汇校本》案的审判结果是禁止了现代文学“汇校本”的出版,这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损害是严重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新版《围城》精装本 “汇校本”被禁绝,这令我们始料未及。在这场争论中,无论是钱先生还是我们,考虑的都只是如何为作者和出版者“维权”,而不是要封杀一种类型的演绎作品。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文学研究确有需要,一些现代文学作品“汇校本”自然就有存在的理由。但这种存在,应该是针对少数研究工作者的,当然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且应当是取得作者授权和专有出版权所有者许可的。 这里关键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根本没有人“禁绝”过现代文学作品“汇校本”,但是多年来无人问津此事,恐怕是这一条限制了出版者的积极性。其实,如果出版者肯于“不以营利为目的”支持现代文学研究,要把“汇校”作为一项宏大事业恐怕也并不难(当然也需要原作者接受)。例如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着文库》,其中很多品种涉及兄弟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但商务“文库版”不以营利为目的,限量出版几千册,与其他兄弟社协商版权使用,多获支持。所以“汇校本”出版者其实大可效仿这种合作模式。话说回来,当年川文社的《<围城>汇校本》被禁止出版,原因并不在“汇校”的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是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了不正当竞争,“违背诚实信用和社会公德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出版秩序”(法院判决书语)。获得道歉赔款的判决结果,是赖不到“汇校”头上的。 对此,龚先生的《〈围城〉汇校本十年祭》里也做了一点反思。他说: “我也想到一些“如果”,或许可以使恶因缘转为善因缘。” “如果《〈围城〉汇校本》发行总量不高达十多万册,只印五千册且永远也卖不完,钱锺书先生和人文社当不会打官司吧?” 这话大致靠谱。果真是这样,双方一定会像陈早春社长说的那样,“兄弟社,好商量。” 龚先生还十分感叹地说: “四川文艺社确实没有得到《围城》作者的书面授权,又确实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十多万地印行,我这个只有权利认字的责任编辑实际上什么‘责任’也负担不了!连封面上的‘汇校本’被挖去,我至今都不清楚系谁人之主张!稍有常识的读者都知道,‘汇校本’三个字就是我弄这本书的品牌呀,我怎么也想不通我的某些同行,为什么这样傻------你们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他意识到,对他这个“失控”的策划人来说,事情的结果可能和初衷背道而驰。进入商品社会以后,在某些出版机构里,图书的出版在商业的刚性目的面前,其学术的追求通常是软弱无力的。我能理解他的一些苦衷。 此外,他提到的另外一事令我感触颇深,文中说: “北京友人代我从潘家园弄来一堆当年各色人等关于《〈围城〉汇校本》官司的多种书信、手迹复印件材料,有钱锺书先生的好几封信,有人文社负责人和人文社版《围城》责编的信,有之前公开赞扬《〈围城〉汇校本》但官司一来就马上向钱锺书向人文社‘说明情况’的京沪着名学者的信,有四川文艺出版社时任社长的信……总之,都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史料价值极高的出版档案,竟然成了龚先生的收藏品! 我已调离人文社多年,对于该社疏于档案管理,我无话可说。 但这可能就是我旧事重提,写下这篇文章的一个动因。 2015年2月5日-7日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 作者系三联书店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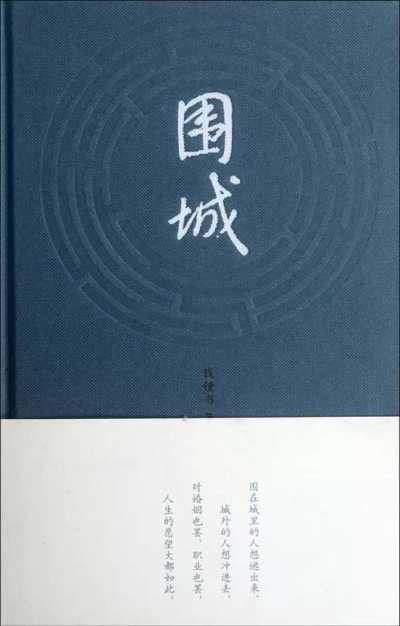
燕南园爱思想 李昕 2015-08-23 08:53:4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