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
(录自《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吴宓日记》无张紫葛三字
带着4000册书逃难!
关于朱小姐
不知仲旗公之名
《观且感》真相
死人教没有出生的人!
《黑夜送别》是捏造
厚诬陈吴二先生之交
颠倒了吴先生
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世人更知陈先生之孤怀卓荦、高风亮节。近有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自称与吴先生为38年的生死之交,是书之作,乃为“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在封底更揭曰:“谨以此书祭奠吴宓,祭奠千千万万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劫中,含愤忍冤殒没的莘莘学者书生;并祈愿,哀恸不再,灾患不再,悲剧不再。”果如此,则其用心立志可谓光明正大,宜乎受到世人的欢迎了。此书确实也曾一度得到不明真相的读者欢迎。以陈吴两先生之一世深交,以两先生之思想与共,以两先生之道德高尚,以两先生之学术覃深,两部据实记述二先生之作,应该可成双璧。然而,细审之下,大谬不然。陆书言必有据,信而可征,根据大量档案资料、文字记载和访问笔录,写出了真实,写出了真实可信的陈先生及其时代背景。张书则多向壁虚造,穿凿附会,虚构了一个吴先生,乃成对吴先生之诬,对吴先生道德人品之诬。虽假托至交,编饬成书,可以欺不明真相之读者于一时,毕竟不能得遂其志于永久。此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也。吴先生乃方正之君子,在世之时,以其方而时为人所欺,想不到逝世十九年之后,竟亦为人织造了一个颠倒了的形象。但是,罔其非道,则万万不能,虽不能起吴先生于地下而辩之,吴先生的友人仍在,吴先生的学生还在,学界人士爱吴先生尊吴先生者多多,辨别是非真伪,大义所在。忝为吴先生弟子,此文之作乃为辩诬。其已见于季石《〈心香泪酒祭吴宓〉质疑》(1997年5月29日文汇报《笔会》)者,不赘。
吴先生一生写《日记》不辍,这已是学界所共知。与吴先生熟悉的朋友,看过吴先生《日记》的人更知道,凡与吴先生有交往的人,即使一面之缘,吴先生也在《日记》中记上姓名及因何得见。数年前,吴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先生《日记》,即告我写一简介以作《日记》注解,说是《日记》中写及我。所知,在上海同时被通知写简介者,尚有同学多人。我们这些同学,当年都读了吴先生的教课,男同学且与吴先生同住在男生宿舍,接触不算是很少,吴先生笔而记之,犹可说。友人王勉,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在联大读书时未选读吴先生教的课程,只是一次日机空袭昆明,在防空洞中与吴先生相遇,交谈数语而已,昨日晤王君,说是也曾得通知写一简介,以备《日记》之注。可见吴先生《日记》不漏相识之语不虚。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吴先生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记》中不见半点踪影?张紫葛为此在书内精心编造了一个吴先生“改造日记”的神话,说是吴先生为了保护这位生死之交,把凡是涉及张紫葛的,全都改造了。不是简单地抹掉,而是彻底地改造,剪裁,重写,装订,等等,一看之下,竟是“天衣无缝”。此等神话,徒令细读《吴宓日记》的季石厥倒,季石《质疑》之文详述其事,人当服其文之可信。《吴宓日记》只此一份,皆如先生在世所写原样,将陆续出版,国人得而共读,张紫葛为此不经之说,勿乃欺人欺世太甚。
张紫葛在书中《后记》(页455)有一段话:“至抗战前夕,他(指吴先生)的私人藏书已逾(按原文误为愈)万册。其中不少珍版善本。南下赴长沙时,他选带了4000 本之谱,其余均寄存在北京亲戚家中。经过长沙南逃,过香港,转云南,所带图书少有损失(振常按,不知是否为稍有损失之误)。于1939年挑了1000余册赠给了西南联大图书馆。1944年至成都,鉴于内迁的燕京大学图书严重不足,他又挑了千余册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按,吴先生于1937年11月7日偕毛子水等离平赴津,乘船至青岛,登胶济火车,到汉口,又换乘粤汉火车,走走停停,于11月19日到长沙(据吴学昭)。路上行程共12天。以一文弱书生(加上陪行的几位)竟能在交通困难、旅途拥塞的抗日战火中,携带着4000册书的重负长途跋涉,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张紫葛先生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他自己能相信吗?
吴先生到成都燕京大学之时,我正就读于燕大,未曾听说先生向燕大图书馆赠书的事。那时我们图书馆的书,的确少得可怜,小小一间书库,大约千余本而已。图书馆主任是梁启超的女公子梁思庄女士,同学和梁女士都常埋怨书少。如果吴先生一下赠书千余册,是件大事,会传开来的。张书中没有提吴先生赠送的千余册书是自己从昆明带到成都,还是后来托运到成都的。按吴先生于1944年8月23日自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到成都,于10月26日傍晚到达成都,时已在湘桂大撤退之后,入抗战后期,交通情况更坏,所以吴先生行程竟长达两月之久,自更不可能带着1000多本书经此长行。为张紫葛解,好在他没有说吴先生是亲带千余册书同来的。吴先生和我们同住在华阳县文庙的男生宿舍,犹忆吴先生只身一人住一小屋,行李简单,书籍无多,孤灯如豆,极为凄凉。此题所谈是极小的小事,虽极小之事亦作伪,大事如何,可知矣。
张书(页269~275)讲了一段所谓朱小姐偕其兄于1953年4月自天津远道来重庆探望吴先生的事。抗日战争开始之前,朱小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吴先生在此校兼课,朱小姐是吴先生的学生。吴先生由北平南下,由朱小姐陪同至天津。又由朱小姐的兄长陪吴先生南下至长沙。据张书所述,朱氏兄妹此时忽来重庆,实因朱小姐在北平时就爱上了吴先生,此来欲圆旧梦。到渝后,才知吴先生已经和邹兰芳结婚,乃向张紫葛吐露衷曲,悻悻而去。张书此前写到吴先生“改造日记”事谓:“1937年冬离开北平一节,删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护吴宓由平逃津;也就一并删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送至长沙情节。理由:如此情节留于日记中,也被认为汝吴宓处处惹草拈花,实为一‘道德败坏之徒’。”(页147)
按,季石所写对张书的《质疑》,谈到张紫葛所谓吴先生删去有关朱小姐情节,季石文发表在《笔会》时此节被删,兹引录季石原稿如下:
“事实上,吴先生现存日记里详细记述了抗战开始时离北平南下的经过。如果真有朱小姐随行,也实不必删。因为吴先生当日照护同行一路到长沙的女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其中有陈援庵先生的女儿陈慈,却没有朱小姐,也没有她的哥哥。当年是如何动身的,路经哪里,乘车乘船都发生了什么事,吴宓日记里可说是巨细无遗。当年的随行者,如今健康、清明如昔,历史岂是可以乱改的。至于朱小姐,确是在北平时吴先生的学生,与她的交往,在现存吴宓日记中也记得很具体。而吴先生日记所记与女性学生或女性友人的交往很多,也往往坦率记录自己对她的观感和想法。这些内容都完整保存,当然也无必要单单删除有关与某一女学生来往的记录,何况日记中有关朱女士的内容历历俱在,并没有删除。”
张书自称在认识吴先生之前,先认识了吴先生尊翁仲旗公(按仲旗公为吴先生叔父。吴先生幼年奉祖母命,嗣与仲旗公为子,称仲旗公为父、嗣父,称自己父亲为爹。先生终生敬事仲旗公,情过骨肉),他是奉了仲旗公之命与吴先生订交的。张书详记经过说,1939年他在重庆,时去于右任家或衙署,“彼时,我见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很受于公尊敬。这就是于公尊称为‘吴公’或‘仲旗公’的贵客。”“既然我们都是于府常客,自不免互相交谈。吴公熟悉经史,尤爱春秋三传,我更少年意气,喜纵谈诸子百家之说,因而一老一少,颇为投机。”一天,仲旗公问张知道吴宓否?方知仲旗公和吴先生是父子关系,即对仲旗公表示早已敬仰吴先生,愿为吴先生弟子,请仲旗公为之介绍。仲旗公表示愿介绍他们做朋友。“大约是1939年8月初旬的一天上午,”张紫葛应于右任电话召去于府,得见仲旗公偕吴先生在座。仲旗公对吴先生和张说:“希望你们做个兄弟般的朋友。”张表示愿对吴先生执弟子礼,吴先生则以为张是宋美龄的秘书而“不敢高攀”。“吴老太爷颇为不悦:‘你怎么说这些生分话?我斟酌久之,才给你们慎重介绍。岂可说出这些市俗客套话。’”于右任拣出张的两篇文章给吴先生看,又说张是“后生可畏”,“将来未可限量”。吴先生当场看了文章两遍,说是“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吴宓就表示,很愿和我切磋学问。但一定要遵父命,作朋友。”张则坚持师事吴先生,还是经于右任一番开导,“就这样,我们订了异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
不惮辞费,引述张书,凡未读张书者,当亦从此段引述得见张紫葛说来似是确切可信了。事实并不然,季石《质疑》文已证,检索吴先生《日记》,不但张书所指之“1939年吴仲旗先生却根本不在重庆,而是在陕西西安。”又证:“事实上,吴仲旗先生在其一生中始终就没有到过重庆。”而张书所谓识吴先生之1939年8月初旬,季石列举吴先生在昆明正忙于所办的各种事务,亦无缘得去重庆。则张紫葛绘声绘色描述的与吴先生在重庆于府订交之事,只能是完全落空了。
事情更有读者所不可能想到的一面,张书既称屡见仲旗公,“一老一少,颇为投机”,仲旗公并为他介绍吴先生“做兄弟般的朋友”,怎么会在他自称“写成《吴宓的第三个28年》(振常按,当即为《心香泪酒祭吴宓》之原拟名),已洽妥,即将出版”之际,于1995年12月3日写信给吴先生幼女学昭,说是“专函请你协助两事”,两事之第一事为“校正我记忆未清的几点”。其第一点,赫然写着:“你祖父和两位姐姐的名字。”天下事的怪异还有过于此的吗?对于这么一位屡见的“颇为投机”的长者,且是生死之交的至友的父亲,竟然不知其名?说是一时记不起来了。张先生在他的《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中,不是以他的惊人记忆力自负吗?且自述所以受宋美龄赏识并得为宋的机要秘书,即由于他的惊人记忆力而起。在这本《心香泪酒祭吴宓》的《后记》中,不是也说他的记忆力绝对可靠,所记“绝对准确”吗?此事有待于张紫葛先生指教。
据张书所述,吴先生于1956年给他看了先生从1956年6月24日至1956年10月4日所写札记一册,共30则不到。张自称印象最深的是两则,一则题《苟不教,性乃迁》,藉为J女生补习古文事,阐发有教无类思想。一则题《观且感》,述吴先生于1956年9月30日晚参加中共重庆市委国庆招待会及10月1日参加国庆观礼情况。(张书页310~321)
张文详述《观且感》的内容及吴先生的感想。张文写得有声有色,长达四页,谓吴先生于9月30日下午乘市里派来的专车,自北碚乘车入城。“市委的国庆招待会,富丽堂皇。陈设华贵,宴馔丰美。宴席连绵,琳琅满目。首尾宴桌之间,遥远难辨人貌。济济多士,其盛大有似欧美之国宴。……一省辖市之国庆招待会都有如此规模,亦可概见今日中华繁荣之一般矣。”“宴罢,接以盛大的舞会。……场内如云之美女,衣履华丽美艳。有短裙半袜,亦有窄裙袒胸,花色繁多,争奇斗媚,却是绝无蓝色干部服。且伊等大多施粉着脂,香气四溢,余乃大为快慰。”当晚宿市委第一招待所,“甲级房间,衾枕清洁。”次日,乘车至市中心解放碑观礼,又是大篇描写,大段感想,无非夸游行队伍之雄壮,堂堂中华之气象万千。且勿论孤怀卓荦、忧道忧世之吴先生能为此庸俗不堪之文,表现出如斯受宠若惊之状态与否,从事实看,1956年中共重庆市委的国庆招待会、重庆市国庆游行,都只是张紫葛先生的虚构,吴先生参加而发抒感想之说,更是张先生的想象。
今据吴先生《日记》,1956年9月30日是星期天,先生整天没有进城。没有什么人送来请柬,自没有什么入城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事,而是在学校宿舍内“终日整理书物函稿”,“至深夜始寝”。10月1日先生倒是去参加了国庆庆祝会的,但不是在市里,而是在北碚区,规模并不盛大,如先生10月1日《日记》所述:“今年国庆节之庆祝游行,一切从简。”所以没有什么招待宴会,也没有所谓的吴先生“登观礼台”,而是:“宓今日携绿帆布铁架义凳(又俗名马乍子),在会场得安坐,免席地。”这一天的《日记》又记着:“晴,热。国庆节。晨7∶30在操场集合,宓偕豫往。入队,与史地系平、陶及吕烈卿(外文系)同列,随校队至北碚体育场。9∶00开会,11∶00毕。从平劝,宓与豫、陶径归,未参加游行。比宓等正午归抵校,游行队亦已散归矣。”
事实就是这样明白。张紫葛公然作伪。他为什么要作伪?看他书中写1956年前后的吴先生,简直活跃已极,对形势极为乐观,屡作“拥护”、“高呼”之谈,尽是趋时媚世之调,甚至于平生不祝酒的吴先生,也高呼“为……而干杯”。(按,张书杜撰吴先生在宴席上喝醋而不喝酒之说,实则吴先生是喝酒的。)《观且感》只是其一。1956年前后,阶级斗争的调子唱得少一些,形势呈现缓和,确有不少知识分子为之欢呼,吴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始终是个远离政治的学者,头脑冷静如初,厌恶政治如初,坚持维护中华文化如初。《观且感》的思想,不符合于吴先生。不多举,只引《观且感》中一句:“今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实应举国上下,万众奋发,致力于科学技术之精进,力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突飞猛进。”这就完全不符吴先生的思想。吴先生诚然赞成和拥护要搞经济建设,但自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先生,多次倾谈,即得共识:“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9~10)是以先生一生服膺中华优良文化,维护中华优良文化,舍文化而言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非先生之意也。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有深交,竟全然不顾吴先生一贯的思想,做此伪托,胆可谓大矣。
张紫葛确实胆大,大到可以公然搬出一个死人来作他的老师。请看下节。
张紫葛记他经张季鸾推许,拜见于右任。其书第三页这样写着:
于右任问及我的家庭和求学经过,叹为苦儿困学。复问师承,我答: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于右任知道吴之英师与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盛赞吴师道德文章。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我简单回答了几句,说:“我拜门时先师年事已高,精力很差,尤其我少不更事,因此学无根底,有玷先师门墙。”
以上所举,已经超越神话,只可于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得之,或者与近年为气死历史学家而编制的“戏说”的所谓历史题材电视剧相近。奇怪的是,编造此说之时,或写作这本“事实可靠”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之时,张紫葛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书?
按,吴子英,字伯朅,吴西蒙愚者,四川名山人。生于1957年(三秦记注:原书校误,应为1857年),卒于1918年。四川尊经书院毕业。1887年后任通才书院主讲、尊经书院都讲、蜀学会主讲、《蜀学报》主笔,推动戊戌变法。入民国后,任国学院院正。着有《寿栎庐丛书》,是一位“熟精选理,尤好诵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文”的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他是反孔健将吴虞(又陵)的老师,吴虞从他“问卿云之学,穷文章之奥”(《吴先生墓志铭》)。据香港90年代杂志社出版的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载《作者简介》:“张紫葛,1920年生于湖北松滋县。”
这就奇了!一个1918年已经死了,一个1920年才出生,死了两年的人怎么去收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做学生,或者说一个死了的人怎么去收一个方呱呱坠地的婴儿做学生。此事之伪,不辩而明。
谎话还有。吴伯朅并无功名,不是什么进士,也不是与章太炎同窗同为俞樾弟子。四川尊经书院是张之洞为四川学政时倡办的。主讲为湘潭王闿运,吴之英为尊经书院学生,何曾去做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执贽俞樾是杭州的诂经精舍,非苏州的春在堂。还有一层,吴之英所长是文章之学,由上引文可明,也就不会有于右任“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的说话了。开口便假,张君何以解释。此事无关于张紫葛之记吴宓先生,读之可作参考。
张书有《黑夜送别》一章(页423~436),写1976年11月吴先生将回老家陕西泾阳之前,在漆黑午夜中,偕刘尊一前来向张紫葛告别。张自称于195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五年,刑满后送回重庆北碚接受“群众管制”。吴先生来向他告别时,他方被斗争了一夜,在回家的路上,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吴先生和刘尊一叫住了,他们就是这样在路边告别的。书中(页433~434)是这样写的:
今日吴宓收到陕西他妹妹吴须曼来信,打算叫她儿子(吴宓的甥儿)来北碚接他归老家度晚年。吴宓决定今晚在这儿和我说几句话。
吴宓:“是啊!紫葛,我可能最近就回陕西老家,……我视力昏,不能自理生活了。……今晚就算告别吧!”
后来,刘尊一告诉我,就在这黑夜送别后的第三天,吴宓的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突然来了。小伙子办事伶俐,先找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办好交涉,革委会同意他领吴宓回原籍去赡养后,他才来到吴宓的宿舍,见他舅舅。
张书又说,吴先生走时,有刘尊一送行。
这里有几件事实须要辨清。一是吴先生被接回泾阳的时间,是在1976年12月。吴须曼在“文革”中,曾三次从泾阳来重庆探望吴先生,最后一次是在1976年12月来的,而非11月。这或许可说是张紫葛记错了,那么,二,吴须曼是在12月到西南师院看见吴先生后,决定接先生回家,经先生同意,并得校方同意,同时电召其子王玕、女婿鲁予生来渝接先生。其事极为仓促,先生何能有暇去向张告别?三,吴须曼之所以决定接吴先生回家,是因为她发现先生眼盲腿折,重病卧床,不能行走。吴先生既已不能行走,怎么可能去向张紫葛告别,且是“黑夜送别”?四,书中所写刘尊一女士,是张的老朋友,张书多次写《日记》记及刘尊一,说是“素不喜其人”,从不来往。据吴须曼回忆,她接吴先生回乡时,只有校方前去送行,并无刘尊一其人。五,同据吴须曼回忆,三去重庆,从未见过张紫葛,也从没有听吴先生提起过张紫葛。这一点,只能留待张先生本人思考了。
张书《淡淡的悲哀》一章(页348~353)厚诬吴先生,厚诬陈寅恪先生,厚诬陈吴二先生一生深厚的友情,不可不词而辟之。
张书此章写了吴先生1961年9月专程去广州探望陈先生之行,开端似为陈吴二先生晤谈做一总结,说是“两人意见一致的是”,这已经够怪了。两位相交多年的至友晤面,畅叙别情,切磋学问,哪里用得着类如发表公报一般的形式,标举一致的意见?而所谓相一致意见的第一条是:“都希望神州大地像1956年那样发展下去。”吴先生未曾对1956年有过幻想,已如上文《〈观且感〉真相》所述,陈先生更是如此,精研学问,撰述名篇,丝毫不为外界风雨所动。管它什么东西南北风,吹不皱一池治学的春水。既写两人意见之一致,就必有不一致的意见,接下去,果然出现了“却也小有分歧”的字样。
“分歧”云何?张紫葛举出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吴先生关于自己思想改造的文章,标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张居然说是,吴先生带去了这篇文章,念给陈先生听了。于是有如此一段妙文:
陈安静地听他念完全文之后,徐徐询问:“文中所言,悉出肺腑,并无造作之词?”“是的。”“秉笔为文之前,即知此文即将刊之报端乎?”“当然知道的。”沉默。吴宓折叠收拾好文章,陈寅恪才说:“他们没叫我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如果叫我写,我也是不会写的。这一点,你比我强。”吴宓默然,未置一词。内心却对陈寅恪的“壁立千仞”并很不赞成。但他未对任何人说过。(振常按,张书原文此段是分行排列,为省篇幅,我把它连写如上)
以上所谓“分歧”,全是捏造诬陷。据所知,吴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屡次检查,未能通过,后在领导和同事“多方帮助”下,勉强再做检查,文章乃被校方拿去公开发表,刊于重庆《新华日报》,相继为《光明日报》及上海《大公报》全文转载,吴先生对自己的违心之言和此种做法极为痛苦,时有自责之语。至同年10月2日有友人告诉吴先生,说是当局已将先生这篇思想改造文章译为英文,对外广播,“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先生在当日《日记》中于此语之后,记下了“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的痛心语言。《日记》中,同年10月3日阴历中秋节,有《壬辰中秋》一诗,写先生自责被迫写思想改造文的违心,诗中有句云:“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末句重申素志:“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此诗可以为先生作证。再引一事以为参证:吴先生是红学大师,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吴先生自不能免被强令写文章批俞。这一回,吴先生是顶住了,坚决拒绝,然对此深感内心痛苦,同年11月19日《日记》云:“自恨生不逢辰,不能如黄师(按指黄晦闻)、碧柳(按为吴芳吉)、迪生(按为梅光迪)诸友,早于1954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痛苦。”对于“批俞”之事,尚且感到如此痛苦,何况是切身所关的“思想改造”之自污乎?对于这样一篇极感痛心的文章,还能加以张扬,讲与人听,又是读给几十年心灵共通的陈先生听吗?其事之荒谬编造,人共识之。再举一例。《吴宓与陈寅恪》页145,引1961年8月31日《雨僧日记》述陈吴二先生是日谈话内容,在“其间宓亦插述宓思想”后,出版时删去数字,意义大变,应为“其间宓亦插述宓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经历之困苦与危机”,原意甚明,对于思想改造与教学改革不满也。
张紫葛的编造不止于此,更深一层的对陈吴二先生的诬陷,接踵而至。紧接前文,所谓吴先生对陈先生的“壁立千仞”很不赞成而未对任何人说过的话,“直到1974年吴宓在本书作者的那间小屋里和作者叙述这段往事时,才一一引举如下。”按张书所述,吴先生所不赞成于陈先生的事是,陈先生对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很欠明智”,“只可解释为故意激恼对方”;红专大辩论,大字报贴到陈先生家门外,陈先生不该生气,不该询问领导,不该提出辞职,不该提出搬出中山大学。如此等等,难于想象张紫葛是如何编织以陷陈吴二先生的。陈吴二先生已逝,说自由我说,但是,张紫葛忘了一条:吴先生广州之行,留下了两万多字的《日记》。《日记》正在整理,陆续发排、出版以后,张紫葛何以对天下人?
张紫葛笔下此事未完。吴先生既有上举“这么几条(对陈先生)不以为然,却是秘而不宣,这岂不是腹诽?少年莫逆之交,乃此腹诽,大非朋友之道。别后,吴宓越想越觉不爽。”于是,吴先生便拟再访陈先生,“俾得坦率直陈,讨论讨论这些不以为然之处。”其实,吴先生计划再到广州,完全是为了视陈先生折膝之伤(陈先生于1962年7月入浴时跌倒,右腿骨折断),吴先生于1963年10月得知此事,因而计划去看望陈先生。几次计划出发,均因故未成。此中过程,详记于《吴宓与陈寅恪》中,此书连同《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曾寄赠张紫葛。张紫葛只顾抄录于他“有用”之处,不惜歪曲和编造其他事实。
吴先生确实对于陈先生说过“壁立千仞”的话,那完全是对陈先生崇高的颂扬。1961年9月3日,在广州,中山大学陈序经先生及夫人请吴先生在陈家早餐,相对畅谈,陈序经先生又谈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习惯且安定矣。”(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页146)则“壁立千仞”之语,可能是陈序经先生的原话,更可能是吴先生听了陈序经先生对寅恪先生情况简介后所作的概括,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显然是对陈先生的最高颂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试问,此种境界,不是对陈先生学问、道德、人格的颂扬是什么?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都以此种境界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箴言,企求达到这个地步。而张紫葛却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加之于吴先生,以为是吴先生加于陈先生的微词,何其妄也!
1961年9月,吴先生自广州到北京,贺麟告诉吴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吴先生进京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贺麟表示愿陪老师去见周扬,先生拒绝了。先生手订的《吴宓自编年谱》(页231)这样写着:“宓惧祸,辞未往。(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惟就此事而论,周扬实为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到了张紫葛笔下,竟又拉扯上陈先生,颠倒为吴先生之拒绝访周扬,是为了和陈先生比高低。张书(页352)如是写:周扬拟访陈先生,陈先生先是拒绝,后经陈序经反复劝说,勉强同意。“到陈序经陪同周扬来访,周扬态度谦逊,而陈寅恪却很为矜持,并且主动问难。说有关领导人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周扬耐心解释,陈寅恪却一再责难。然而周扬始终彬彬有礼。”(振常按,周扬后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他那次“不该激怒陈先生”。张紫葛何以解!)张书接着说:“陈寅恪以周扬来访,矜态相见。吴宓上访周扬,还请贺麟先容。我吴宓与陈寅恪情同手足,学问虽自愧弗如,品格历来相同。奈何今天在周扬名下高下差别如此?两相比较,能不自愧?”这是张紫葛论定吴先生拒访周扬的一个理由,只能说是以己之心度君子。
陈吴两先生一生的友谊,吴先生对陈先生的佩服尊重,两先生心灵相通,患难与共,世所共知。张紫葛先生只顾自做文章,全不考虑。为了提醒张先生,于此稍加摘引陈吴二先生相知之深的证明。1919 年哈佛初识,倾谈定交,终身皆秉初旨。《空轩诗话》有文述:“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陈吴两先生哈佛对谈的内容,陈先生所谈对于吴先生影响之深,具见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引《雨僧日记》,可为佐证。此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两先生所谈更广更深,关系于中国文化之前途,立身处世之道,以及立学之本,亦可覆按。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沉,对于两先生影响极大,陈先生以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作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先生在写成此文前,对吴先生谈了以上观点。吴先生谨受教,而表示:“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这是两位大师、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怆壮烈之语。吴先生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有感写成《落花诗》八首,痛陈文化衰落之苦,可参。因而,吴先生乃有王静安先生灵前之誓:“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吴宓与陈寅恪》,页43)到了“文化大革命”,陈吴两先生果然以身殉文化了。
正唯陈吴二先生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认识和理想上,是真正的知音,便两心相通,至死不泯,况之古人,伯牙子期,也不过尔尔,是以才有彼此间的关切。1961年,吴先生有广州之行,后又多次计划再去广州,是一例。而在1971年9月8日,吴先生还戴着“牛鬼蛇神”帽子,在四川梁平劳动改造之时,竟以无畏的勇气,写信给中山大学,探问已经逝世两年的陈先生下落。这不是一般常人之情,非心灵相通如二先生者不能办。小而至于,1944年吴先生之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燕京大学授课,就是因为陈先生到燕大去了,“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按为萧公权先生)共事共学。”(《吴宓与陈寅恪》,页110)甚而梦寐之间,吴先生亦念及陈先生。如1952年12月30日,《日记》记:“28日未晓,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吴宓与陈寅恪》,页133)1971年1月29日《日记》记:“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①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②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吴宓与陈寅恪》,页154)1973年6月3日《日记》记:“阴雨。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 再醒。适梦陈寅恪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陈吴二先生作诗唱和、互道衷情之作甚多,备载二先生集,不引,只转介未曾发表的吴先生一首诗之数句。上引1952年12月30日《日记》“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后,紧接“乃作一诗怀寅恪云”。其诗前四句为:“两载绝音响,翻愁信息来。高名群鬼瞰,劲节万枝摧。”第二句云“翻愁”,当指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可为前述对“思想改造”之痛苦感佐证。后二句自指肖小之徒对陈先生的攻讦。末二句为“昆池呜咽水,只敬观堂才”。自是言陈先生独佩服自沉昆明湖的王静安先生,亦可移用于吴先生以陈先生比王先生,而独佩之。吴先生向以“受教追陪”于陈先生为荣,吴先生1959年7月29日《寄答陈寅恪兄》诗“受教追陪四十秋”可证,吴先生结识陈先生后之行事可证。
本节文字写来较长,窃以为陈吴二先生之素志未必为人所尽晓,而二先生毕生相知之深,相交之笃,实是古道不泯,乃竟为妄人所歪曲和伪造。辩之,不只为止妄人之口,且为明正道、正人心也。
吴先生一生为保卫中华优良文化,献身学术,乐道,明道,卫道,远离政治,与现实政治无涉。先生早年有“二马之喻”,即一面欲图事功,一面欲“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着作”,先生曾欲兼得此二者,所以喻为“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面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1927年6月14日《雨僧日记》,据《吴宓与陈寅恪》引)先生所谓事功,不是入世谋政治上的事业,而是以自己的力量,组织人谋学术文化的发展,那就是先生与志同道合者创办《学衡》,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独力主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筹办并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等等。这一方面的事业,和先生毕生研究学问,培育青年相并进。先生是以学人而兼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组织者、倡导者与保卫者。先生毕生乐此,对现实政治不只远离,而且厌恶已极。“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之时,先生甘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大不韪,而反对批孔,即是反对政治干预学术。与朋友交,不言政治,只谈学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变了一个人,不但热衷政治,分析形势,趋时媚世,乐在其中;对于他在解放初期享受的政治待遇,极感自得。还乐于“见大人”,如书中所谓的求见邓小平(尽管不是为自己)。甚且杜撰给毛泽东、邓小平算命这样厚诬先生的不经之事。甚至于说,1956年匈牙利事件初起,先生竟能联想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一定会紧起来,这在一个纯然不懂政治的吴先生身上,绝无可能。
吴先生为人光明磊落,方正纯朴,心口如一,从不作谎语,不知如何应付人事,或可说是迂,或可说是书生意气。因此,一生做过不少在旁人看来是傻事,在先生看来,则是道之所在、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庸俗的人。这又是厚诬吴先生。
甚而在恋爱上,吴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热恋毛彦文,原出于抱打不平,既经卷入,光明正大,从不隐晦。张紫葛何能知此,拉出了个朱小姐千里寻先生,而先生呢,张书把先生写成一个庸俗的人,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与朱氏兄妹分别,先生对张“轻轻叹了一声,念了一句仿《西厢记》崔莺莺的道白:‘叹人生,烦恼填胸臆!量这般大小的车儿怎生载得起!’又转头对我说:‘此词难谐我意。你别误会,我并没和朱某恋爱。过去不曾,现在更没有。’”(页275)先生不管是否恋爱朱小姐,都不会这么说。当年恋爱毛彦文,先生公开发表诗,有句云:“吴宓苦爱□□□,三州人士共惊闻。”何其襟怀坦白。这种境界,非庸俗人所能理解。张之出此,良有以也。
全书写吴先生日常说话的语言,简直是不堪卒读。无论何时何地,书中的吴先生,一开口便是腐朽恶劣的文言,没有半点活气。吴先生无论讲课,还是日常交谈,从来是现代语言,没有书里这种怪腔滥词。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相交三十八年,对于吴先生的语言竟全无所知,也就够奇怪了。
读过全书,写成此文,期待张紫葛先生有以指教。
1997年6月8日至10日深夜
唐振常 2011-04-11 20:21:15
 |
相關閱讀 |
 |
推薦文章 |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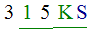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