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的困境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今年3月28日,于建嵘与秦晖、冯兴元、王度、朱学勤(担任主持)等人在北京言几右书店参加《访法札记》读书沙龙。通过“观察中国”,于建嵘先生希望能与读者分享他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省思。由于全文较长,观察中国择其精要刊发。 感谢于建嵘先生对“观察中国”的热心支持。 于建嵘:今天非常高兴到这里来。特别是秦晖老师以及王度先生、冯兴元先生都过来,朱学东做主持人,应该参加这个活动,而且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 这本书已经写了6、7年,这与我的工作习惯有关,我做社会学研究,到了什么地方喜欢写日记,包括今天也会记下来。很多日记写下来后,很多年后翻出这些日记,当时的思考在今天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很有意义。 这本书是工作记录,写作与法国使馆有关,早些年他们找我做了一次访问,按照我的意见去访问,我说要访问什么人就访问什么人,全部是按照我的构思去做,他们没有指派主题。我当时的构思主要想了解法国的工会和农会,那时候每天找这样的人,如何谈话如何了解。 这本书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有明确的法定权利。法国人对自己的权利非常明确,知道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东西不是他的。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一个和谐社会,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一个救济渠道,必须有司法、有组织、有人帮他。那为什么法国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参加了许多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组织保护他不同的权利,一个农民参加了几个工会,这个工会管这一块,那个工会管那一块,而且工会之间有竞争性,工会保护我的利益就加入,不保护我的利益就不加入,这个工会自然而然就没有生命力。 所以我访问了很多工会的领导人告诉我,我们必须为会员服务,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一旦权利受到侵害,有利益的表达,还要有开放的媒体。 书中间有一段话,关于法国共和国宣言。他们说共和国宣言类似于中国的信访制度。其实完全不是,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权利,《共和国宣言》调查完之后,怎么发挥作用?他说我们有核武器。什么叫核武器?他说可以通知媒体。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对付你,但我可以把你公布到媒体上去。所以有议会,有代表他的组织,有开放的媒体。 我想写这些东西,根据我的观察、根据我的想法。当然这本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考察农会和工会,没有对法国进行全面的考察。原来我的书的题目是“寻找法国社会和谐的基础”,因为当时法国发生了动荡,05、06、07年我都去了,所以这本书也不算什么书,就是一个工作日记。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中国或者对未来社会影响很重要的力量是第二代农民工。 现在大家知道讲农民工,从数字来讲一亿五千万,真正的农民工第二代是一亿二千万。还有一批人是在城里生长出来的农民工第二代。这两个农民工跟第一代农民工有区别:第一代农民工是种过地,再去城里打工的,目的非常简单,是赚钱回家建房子、讨老婆、送孩子读书。 第二代农民工很大的问题是都从学校里出来,这批人有一个特点是对农村、农业没有多大真正的认识。 我去法国后,跟Jean-PhilippeBEJA有一个对话,书里有写。到深圳问那些农民工,就问他们对未来怎么构想。基本结论是,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但我肯定不会回去。我问那怎么办?有些人说,假如我想的话,我现在赚的钱,将来找一个老婆,在县城里买个房子,开个小铺面。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漂移的社会”,对农民工第二代的思考,这跟法国社会骚乱的一批移民第二代有关。当时我写了一个内参,发表在《改革内参》上,我非常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但有一些分解。今年过年期间我跑了五个市,采访了农民工第二代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有一些地方都存在,有一些户口改革后,小城镇可以随便进去。 今年调查我发现,有一些农民工在小城镇买一个地方,开一个小铺子,逐渐往外面转移。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认为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问题,这个过程一直存在,因为社会大转移,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移,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移。 不过法国有一个经验很重要,要不要把这些人聚在一起?我到法国访问的时候,警察局讲了一个问题,把这些移民二代聚集在一个地方是不对的。所以当时我想了一个问题,假如大学生全部聚在一起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农民工问题,将来安排移民的时候,地方不应该把他们太分离。 我是反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我非常希望农民工的子弟上学,但我反对建单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应该跟其他学生融合在一起,而且我反对把那些人都聚集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紧张地工作,那些连摆摊的地方多没有。当年我访问安源煤矿的时候,他们说我摆地摊都没有人,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没有钱。他们应该交叉生活,融入社会。 这个问题的思考,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解答,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移民、流动人口的问题,所以我说在漂移的社会中进不了城市又回不到农村,在城市和农村边缘漂移,对中国将来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呼吁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第二代和农民工第二代的未来,要重视农民工第二代的未来,也要重视农民工第二代的权利问题。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不是农民工的人也在漂移,我们在北京漂移,没有北京户口,将来怎么办?北京买不了房子,可能很多年才能买到房子,这都是问题。这个社会漂移的过程中,会带来什么问题我认为要观察,今天谁都难以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 当年广东发生两起骚乱时,我赶到广东,骚乱发生的时间分别是11年6月1日和6月11日,全是第二代四川农民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但是我的看法是,可能目前又有缓解,但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秦晖: 首先祝贺于建嵘这本书的出版,于建嵘走了很多地方,我跟他一起去过一两次,是我陪他,不是他陪我。但是很抱歉、很遗憾,没有像他有那样的心得,而且那么丰富。 法国我也去过几次,我们对法国农民,我想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第一印象是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一句话听来的,说法国农民是一口袋马铃薯,没有组织,不能代表自己,只能由皇帝代表他,所以把拿破仑三世选上去,法国农民是最反动的。 后来我感觉,今天法国的工人组织能力远远没有农民那么强,欧洲各国的农民现在占总人口的比重其实只有10%上下甚至更低,但他们就能影响整个议会大多数的投票。说实在的,比工人还要厉害。 这些年整个欧洲工会衰落,但是农会很厉害,正好相反。所以我觉得人有没有组织能力,根本不取决于你是农民还是工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你有没有权利,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动物,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不会结社,只有允不允许结社的问题。 我们有些人老认为外国人喜欢结社,中国人就喜欢当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跟谁都不搭理,哪有这回事?根本不是。 所以第二个,法国农民问题现在根本就不存在,真正要说法国有问题的,是于建嵘提到克利希苏布瓦的一些新移民,从民族构成来讲不是法兰西人,大部分是来自马格里布地区、来自非洲,从信仰上是穆斯林,从人种讲大部分是黑人,这些人成为法国的新移民,他们在法国的权利和怎么融入法国成为很大的问题。 至于法国农民早已经不是问题了,假如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问题。印象很深的的当年我们加入WTO谈判的时候,当时我跟一个法国人(越南裔,欧盟驻WTO多哈和会谈判农业和会的欧盟谈判代表)谈,他跟我说我很不理解你们中国——大家知道在多哈和会中谈判其实就是保护农民保护多少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有保护农业的传统,有很高的农业补贴,美国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在多哈和会上为这个事情争得不亦乐乎。 中国加入的时候,中国理论上要争取有保护的权利,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好像是保护的比重应该是15%。美国说不行,你不能享受这个东西。中国最后就让步,结果我们接受了一个8%的比例。 他觉得很奇怪,你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左派掌权,为什么向新自由主义投降?我们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有15%的保护,你们太堕落了,怎么向新自由主义投降,才8%?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对抗美国?为什么站在美国一边? 后来我说,你要搞清楚,这个8%其实是我们要争取一个话语权,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才这样要求的。我们真正对这个补贴的限额,说实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WTO谈判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取消农业税,如果真的要讲,中国当时对农业的补贴程度是负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农业那里抽取的,而不是补贴的。当然和现在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所以对中国来讲,农业补贴的力度多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还要争它,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地位,不愿被人列进发达国家而丧失了代表南方一大帮国家说话的老大资格,对于补不补贴根本不在乎,也从来没争过这个东西。 其实这位先生还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他本人不是法国人,而是越裔法国人,是越南人,当时是越南的一个孤儿,被法国传教士收养以后带到法国在法国成长,现在成为法国着名的外交官,成为整个欧盟WTO谈判中的首席发言人,他对东方不是不了解,但仍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够想到中国这些事儿。所以我的感触很多。 冯兴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这本书我昨天、前天都在看,感受很深。 首先,法国的农民已经实现了英国法学家梅因讲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标志,发展到现在,农民从身份到契约完全完成了。契约背后就是基本权利。现在法国的农民把很多权利抓在手里,同时抓很多权益,各种福利各种补贴,一手抓权利,一手抓很多的权益(给你的权益)。 这种状况我几年前接待过欧盟自由民主议会党团的成员,里面的法国朋友是议会成员,他们都是支持农业补贴的。德国自民党的朋友完全不一样,德国自民党讲经济自由,这里面分两派:一派是支持欧元比较少,欧元是集权的标志。一派觉得欧元是减少交易费用的一个机制,应该统一货币。 由于希腊危机的出来,两派冲突加剧,自民党一部分人退出来,建立了一个另类选择党,具体中文怎么叫我不知道,尽管以前我长期研究德国的,但我是研究制度的,后来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再看。 从德国人角度来看,德国最失败的三个产业政策为:第一,农业政策,因为需要大量补贴。第二个是船舶业,也需要大量补贴支撑。第三个是煤炭业。这三个的特点都是维持着一个陈旧的产业机构。 产业政策有两类,一类是支持新机构的形成,一类是支持维护旧的、已经过时的机构。也就是说当你保护落后的,等于你在阻碍新的结构的形成。 法国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产权在私人手里,和“权分”连在一起,所以农业市场是发达的,交易是活跃的,有大量补贴。而且法国是大的农业国,很多产品是过剩的,如牛奶。以前也发生过把牛奶大量倒掉,因为不降价,宁可不卖。 我看于建嵘这本书所讲的,中国一看就会想到农业的目标是保障供给,但是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农业的目标大概有五个,有供给目标,有安全目标,有生态目标,有观光目标,有很多。 法国农民说,现在还要给我补贴,给我们生态,生物多样性都是需要的,这实际上就是公共产品,不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我维护一片绿地或者树林,树林相当于人类的肺,这不是我个人要用,而是整个法国和整个地球都需要,是一个公共品。怎么看补贴?刚才讲的补贴有一定的正当性,在生态方面,如果服务这个目标的话。 第二,如果是农业科技,新的科技,由于最初投入大,而且法国农民主要是家庭农场,跟德国一样,所以你让家庭农场去搞科技创新是有限的,所以需要组织化的,如合作社、农协。法国有三个组织非常有意思,书里写到:农业议会、农业工会、农民协会。 法国除了行会性质的,其他都是自愿参加的,那个非常好,不像德国那种,我们叫做社团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而且是法定的,大家都要参加,德国工商会就是如此。法国工会发展非常大,但看这本书,人数好像只有二百万,很吃惊,没想到,因为法国工会罢工时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德国。 去年我在德国,正好碰到德国联邦铁路罢工,不是全部罢工,而是把干线给断了,把你的时间表全部打乱,因为只要断掉一部分,在购票机买的票显的时间就不对,说没有这个线,没有这个线也能到,因为德国的火车票是在某一个站可以转达,同一张票,很简单,但很不舒服,包括你通知朋友的时间全部乱了。 飞机也是如此,原来是坐汉莎,取消了,火车的时间不行了,要转到柏林航空公司,没坐德国之翼的飞机。这些让你不舒服。法国的工会破坏力非常厉害,估计法国企业家会非常怕罢工。 王度(艺术家,长期居住巴黎): 关于法国社会、法国农村、法国文化、政治方面的话,都是非常好,我觉得他们理解我的国家比我理解的还深。既然来了,我说几句话。 第一,我听他们三位说的有些非常对非常正确,有关是法国农民、农村、农业各个方面的重要性都非常大,文化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方面都非常重要。虽然今年在法国做农民而且做农业人的数量并不大,很少,但他们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三位老师都提到这一点,法国做政治的人、政治家,尤其是法国总统都非常尊重,甚至有的时候很怕农民的想法,农民会说什么话。 比如在法国每年会在农业馆举办很大规模的农业展览,邀请法国各个地方的农民、做农业的人到这里介绍他们的食品。法国所有政治人,不管男女不管年龄,都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活动,表示他们对农民的尊敬和关注。这个肯定是一个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 现在法国城市化过程已经很完整,但是农民还是很重要,每一个法国人有机会,你知道法国人夏天放假时间比较多,肯定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看自己的祖先原来住的地方。这个现象跟中国有些像。 我从来没住过法国农村,但我的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都是农民,我们从住的地方回到他们那边,每年几次去那里看一下,跟住在农村的人说话,了解到农村的问题,以及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非常重要,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我们不认为我们是真正的法国人。 刚才秦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从非洲移到法国的人,遇到很多障碍,包括受歧视方面的问题,可能跟文化、宗教、民族有关,可能也因为他们在法国没有自己的农村、自己的老家,没有根,这是一个障碍。 我的母亲从法国西北部来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这些人一百年前移民到巴黎时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当地人看到他们不是真正的法国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让别的国家移民到法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主要的。 农民农村之所以有政治重要性、文化重要性、社会重要性,我觉得在很多法国人眼里,也是那种能够保持法国的传统、法国的文化,以及法国很多很重要方面的问题。所以每个人回到农村时,会特别尊敬,因为他们懂每个地方的历史、每个地方原来的传统、每个地方的方言、每个地方的一些事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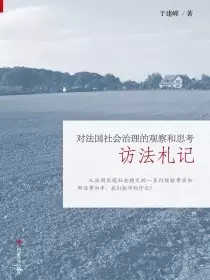





观察中国 2015-08-23 08:54:2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