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曾彦修:他把枪口抬高了一厘米 纪念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昨日凌晨4点43分,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杂文大家曾彦修先生,即严秀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 曾彦修先生是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夏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3年调中央宣传部。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据介绍,在“反右”中,曾彦修曾把自己划为“右派”,轰动全国。当时在“反右”中,曾老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他认为没有什么人应当划为“右派分子”。上级追得紧,而且还有“百分比”。曾老作为一个领导,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上面下达的“任务”,于是把自己作为“右派”报上去。曾老被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1960年到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着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京沪竹枝词》等。 2011年,已经年过90岁的曾老先生开始写回忆录《平生六记》。在这本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平生六记》于201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在《平生六记》中,曾老先生用这句话作为这本回忆录的开场,这也是他一生最问心无愧的地方。而在《九十自励》诗中曾彦修先生写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曾彦修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6 1950年初,即全国解放的一年多(有些地方才几个月,如广东、四川、云南等地)后,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最大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恐怕整整有近一年或一年多,是最中心的工作。天天要向北京报告镇压人数(“镇压”,长期以来的死刑代名词)。这个运动为什么叫“大张旗鼓”呢?就是这是一切工作中心的中心,随便你火车站、菜市场、电影院、医院、公园中,都必须贴满大标语,牵起大红布的口号,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须是满墙满壁的大标语口号。 报纸更是几个版面都是“镇反”宣传品,前后总要宣传好几个月。各大学(以至中学)、工会、青年团、妇联,特别是各街道居民委员会……更是长时间学文件、读报纸、开控诉会……总之,凡是进行这项任务的,党、政、军、民、学,全民各界,都要事先宣传到,同时充分揭露到、控诉到,确是成了一个时期大中城市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那一两年,对这件事是:公安管实行;党、政、军、民、学、宣则长时间管宣传活动。 广州是 1949年 10月初旬后解放的,敌人前几天就全部跑光了,我大军是在敌军全部撤退后昼夜兼程赶进广州城的。 北京是 1949年 1月解放的,上海是 1949年 5月解放的,南京比上海更早一些。以地下工作来说,广州虽然也很可观,但比起北京、上海来,恐怕还是要差一截。因此,广州的广大市民,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了解程度,比起上述城市来当然也就有相当的距离。何况地邻港澳,反动派利用港澳为基地而做的反共宣传的影响,当然在全国是最深的。 上面这些说明,似乎全是废话。其实这些是说明本节问题的根本背景资料,不然你就无法理解本节所述问题的重要性。 1951年快 4月底时,我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我和杨奇分任正副社长,另一总编辑,似新来不久。近 4月底,一晚九时后各有关同志,如采访部主任曾艾荻、编报部主任吴楚、编辑部秘书陈鲁直等六七人正在商议决定明天四个版面如何安排时,采访部政法组组长成幼殊(女,地下党员),忽然紧急拿来政法组记者刚从省公安厅紧急拿回的,明天要处决一百四十多人的名单,和每个人两三行的罪状。 我说,坏了,坏了,我们事先没听说半个字呀,怎么能配合宣传呢!?大家通通变色了。因为大家都看了近一年的京沪各地报纸,知道大镇反一来,报纸是必须同时推出四个版面甚至是加页,集中持续宣传此事的。而我们则刚刚拿到罪状名单,明天如何见报?我们没有社论、没有事先写好的大量控诉资料,没有社会名流支持的谈话,没有受害者对死刑犯的控诉,任何宣传资料都没有,连个社论也写不出。何况一次处决一百四十多人,历史空前,新区群众如何能体会这些!?我们报社乱成一锅粥,都认为明天绝不能这样出报呀,怎么办呢?中央的方针明确得很,是强调大张旗鼓,即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要让群众家喻户晓这些人的罪恶。 同时,我们看见,这当中确有一些曾是杀害我们重要着名人物(现已记不清了)及 1927年时杀害苏驻广州总领事的执行连长。其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又从香港公开回来的,这人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 此外,我早在延安或进北京前在西柏坡时,就听说过或听过报告,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记得好像有沈钧儒、黄炎培)对我们善意地提过意见,说,你们镇反时,总是“公审”,罪名总是“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之类,这怎么行啊!(说不定是 1949年 3月进北京后才听说的。) 我们这个“编前会议”,苦了两个小时,连十一时的夜餐也端进来了,只是没有人吃得下一口。大家毫无办法,我们有什么发言权呢?我们的义务就是照登不误,标题越大越好。 如此苦恼了两个小时,毫无办法,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忽然,副社长杨奇同志说,“现在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由老曾同志打电话给 203 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广东初解放时,叶剑英同志的代号是“ 203”。半夜三更我又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呢?原来当时有这么个规定,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在后半夜打电话与党委主要负责人。因为第二天出不了报,对党委主要负责人来说也是个麻烦事。大家又议论了半个小时,都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我说,规定是规定了,谁敢实行?又议论了很久,我说,万一是“ 203”看过的呢,这个钉子可碰的大了。 再议论很久,这回主要是分析叶帅知不知道此事,看过这罪状没有?我说,分局每周一次扩大会,我参加的,但上一二次没提起过这件事情,从这点看,“203”可能不知道。再说这个罪状,“203”长期在蒋区做上层交往工作,论道理他是不会接受按这些罪名去处决人的,这种处决罪名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做法,连我们都接受不了,他会同意吗?这样分析来分析去,杨奇特别同意后一说法,这种罪名“ 203”不会同意,他说,恐怕只有与“ 203”打电话一条路了。我横下一条心,大着胆子就打了,时近午夜十二点,打与他的身边秘书。秘书那儿倒也顺利,说他先去报。约十分钟后,“203”本人来了,“203”先说: “你是曾吗?这事你有意见吗?这可是毛主席定的政策啊,你有什么意见!”我说,“不是,是具体情况太奇怪了”。我只能简陈几分钟。叶帅又反复问,我说“真是这样的,……所以我要报告”。叶帅回答说,“好,你在一点钟前赶到小岛。”东山小岛小区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与叶帅的住地。我立即出发。见省府常务副主席古大存、华南分局另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已先到,另有分局办公厅主任林西,叶帅的主要秘书姚天纵已在座,第三书记方方出差了。我到后不久,叶帅也下楼来了。不久,省府厅长(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华南分局社会部一处长同时也很生气地来了。那个处长把身背的两个麻布口袋的材料往地下重重一丢,二人均有怒色。坐下,叶开场几句,即叫我发言。我讲完,对方也讲情况,说今晚分局社会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等均漏夜办公,参加这一具体行动的(包括沿途及周围警戒的)有一千多人,一切均已准备完毕,准备明天,不,今天九点执行。我一声不吭,知道对方名声很大,在江西时代就是做此事的。 叶帅再叫我讲,说“报馆”有点意见(这些老前辈用词多是老习惯,把我们叫“报馆”),听他们也讲一讲。我就大致讲了上述意见。李凡夫也发言支持我,说,我们宣传工作全不能配合,也是违反中央指示的呀!对方反复讲准备了两三个月,今晚一千多人漏夜办公,不大好办了。跟着古老(古大存,省府常务副主席、华南游击运动老负责人,延安整风时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也表示,他也不知道此事,只有一个空洞罪名的东西,“一贯反动,民愤极大”,怎么行呢?对方反复坚持,一切已完全准备好,要改变影响也不好。 叶帅很沉着。他说,这么大的行动,分局事先不知道。对方立刻反驳说:“分局开会讨论过。”叶说,“那是原则性的,决定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报馆也参加了,知道的人很多,那是个内部动员会,不是行动指令。”对方再三强调他们只是在执行中央与分局的指示。叶帅回答有点刺激了:“要不是报馆通知我,这么大的事情我也要明天看报才知道呀!”古老说,我也是,用省法院的名义,我根本不知道。对方又说,“大张旗鼓”,我们没有那么多宣传干部呀(作者按:那时,“笔杆子”这一词还未出现)。接着,李凡夫立即回应:这事是全党动员呀,我们还会找不到宣传干部吗?总之,说来说去,对方并未让步,坚持明天执行已难于更改。这时,叶帅不得不把最后的重话讲出来了,说:“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叶帅已下了最后的决心。对方当然更知道,叶帅已讲了最后一句话了,立即很不满地说,我通知明天停止执行!于是就离座到厅内边上打了一个电话:明天停止执行!等一会儿又说,“是,全部停止执行,原因等我回来再说。”之后我说我也要打个电话,报馆也是一百多人在等着我回话呢。那里只有一部电话机,我也只能在那里打。 之后,就由叶帅指定林西、李凡夫同志,草拟内部开动员大会与组织宣传队伍,遵中央规定,要做到家喻户晓,每个居民小组都要开宣讲会,声讨会。 重新整理罪状事,叶帅说,这事是报馆提出来的,就由报馆抽人去重新研究和起草草稿(指布告)吧!我说,我两天后就要带领华南代表团去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第一次会议,会上就决定先由报社副社长杨奇带领一个队伍到公安厅去帮助他们整理材料。 我可能是 1951年 4月 26或 27日离开广州去北京开会的。两个星期会完后,我们队伍应上海市委宣传部之邀,往上海走一趟,因为我们中有人未离开过广东、海南岛,所以很想多走几个地方看看。 5月底了,我回到广州,已执行了。具体情形,我就无权再过问了。但为什么又拖这么久?杨奇说,我们几人是到监狱办公室去工作的,材料乱得很,很难整理出一个个人的明显事迹来,所以拖了个把月。我说,还用“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吗?杨说,这个取消了。 又过了几十年,大概是二十世纪末,陈鲁直、成幼殊夫妇作为外交部的离休干部与我同住方庄,我因行动不便,闭门不出,他们来看我。我详细问过成幼殊两次,成说,是乱,是杂,材料不具体,我们开始去四个人,在监狱办公室办公,有两个新党员,不起什么作用,不久,就是我跟杨奇两个人了。我问,人数有什么大变动没有。她说,没有大变化,重新摸了材料,把空洞的“一贯反动”的一类词改为一些具体罪行。但应如何具体处理,我们就无权过问了。报纸当然准备了很久,算是大张旗鼓地做了一些宣传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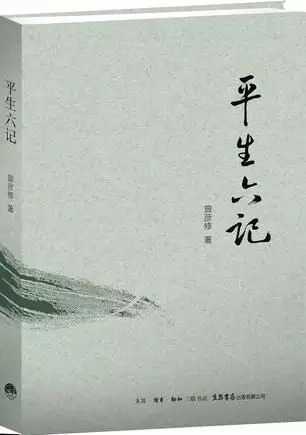
《平生六记》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5:56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