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思享】同一个诺奖,不同的命运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作者:陈为人,山西省作协前副主席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 早在二战后的1946年,英国几位作家就建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此后,每年都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候选人,年复一年讨论达五次之多,但一直未最后决定。尽管诺奖评委会对评选严格保密,“不到火候不揭锅”,但仍有风言风语传出。国外有文友求证于帕斯捷尔纳克,他回答说:“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传闻,我知道的比大家都要晚……与其说我期望,还不如说我担心这一流言会成为事实。”帕斯捷尔纳克还说:“比利时、法国和西德的报刊上都曾谈及此事。人们看到、读到那些消息,也就谈论开来,后来人们从‘BBC’电台听说,似乎本来是我被提名,但有人考虑到当时的世情,便请求提名机构同意让肖洛霍夫替换我作候选人。委员会否决了该项请求后,提名海明威为候选人,也许奖金会授给他……” 向来公允的诺贝尔奖评委会毕竟也是“地球人”,也受到当年两个超级大国“冷战”思维的制约和牵累,作为非艺术的考量和政治上的权衡,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传言成真”,授予了美国作家海明威。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书在苏联境外出版后,立即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瑞典皇家科学院重新考虑把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当时苏联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话中有话地说:“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明确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肖洛霍夫更为合适。 几经戏剧性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还是授予了帕斯捷尔纳克。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蜂涌而起予以热捧,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日瓦戈医生》一书的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日瓦戈医生》是一本“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但冷战时期这种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思维模式,硬是把帕斯捷尔纳克强行推上了政治舞台。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的作品辩解说:“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就武断地认为是“揭露出专制王国铁幕的‘杰作’”,这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 西方的热捧实际上是给帕斯捷尔纳克帮了倒忙,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1958年10月25日的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着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25日的苏联《文学报》上,也发表了《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一文,光从题目看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火药味。 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 1958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决不追究,实际上是发出了“驱逐令”的威胁。迫于这种形势,帕斯捷尔纳克于l2月29日宣布拒绝同一个诺奖,不同的命运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电瑞典科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 帕斯捷尔纳克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检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的基础。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都历史地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正宗知识分子遭到毁灭。”帕斯捷尔纳克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不要把他驱逐出境。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反而使帕斯捷尔纳克因福获祸,在随后的日子里,是一个接踵一个的灾难。他此时写的《诺贝尔奖》一诗,颇能反映他的心境:“我算完了,就象被围猎的野兽……我可倒底做了些什么坏事,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 1959年3月14日,帕斯捷尔纳克在散步时,被从住地别列捷尔金诺传唤到莫斯科接受审问,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威胁道,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再不停止与外国人交往,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就在痛苦和压抑中死去。 肖洛霍夫获奖后 与帕斯捷尔纳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肖洛霍夫的获奖。 1965年,肖洛霍夫终于如苏维埃政权所愿,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仅仅事隔七年后的这次获奖,却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和热捧。报纸刊物上几乎一个口径地说:“这是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并且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七年前因把诺贝尔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攻击,改口说:“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灵已经照亮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得了世界的公认。……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等等。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出版后,曾遭遇过与他的同伴帕斯捷尔纳克相似的命运。马上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当年许多着名的作家、评论家抨击小说歪曲了国内战争,偏离了苏联的革命文艺路线,是“为白卫军说话”。只是由于得到了高尔基的鼎力支持,小说才得以出版。但到第四部出版时,苏联评论界再次产生激烈的争论,有许多“上纲上线”的批判意见,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肖洛霍夫犯了严重的错误”。 面对当年所有苏维埃作家的共同生存境遇,肖洛霍夫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和智慧”:肖洛霍夫笔下的作品,既有属于主流文学的颂扬倾向,又有反映边缘文学的批判特征,处于主流文学和边缘文学的模糊地带。肖洛霍夫采用了“打擦边球”“见了红灯绕着走”的生存策略和写作策略。他极善于对领袖察言观色,得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领导人对他的青睐,成为“三朝红”;他极善于对现状审时度势,在一个接一个针对文化领域的运动中,能有惊无险地“安全着陆”;他很能把握分寸,清楚什么时候该冒尖,什么时候该缩头;他很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什么时候该激昂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不语,什么时候说话可表现作家的个性棱角,什么时候说话必须罔顾左右而言他;他深谙“石油换大米”的交换原则,以某种妥协得到出版的机会,以局部的牺牲获取关键的成功;肖洛霍夫以自己惊人的聪明才智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肖洛霍夫是苏俄文学史上唯一一个既获列宁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既能为对苏联持批判观点的西方知识界所称许,又能被本国统治阶层所接纳,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肖洛霍夫真可谓左右逢源。 苏俄文史学家提出有“两个肖洛霍夫”的观点。一个是作品中所显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苏联文坛上所表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事业摇旗呐喊,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进入自己文学世界,作为民众疾苦的呼吁者,求真求善的寻道者的肖洛霍夫。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这样高度赞扬肖洛霍夫:“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然而,肖洛霍夫并未“文如其人”,与作品中展现的形象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坛的口碑很不好,留下了许多劣迹: 肖洛霍夫嘲讽地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寄居蟹”,不言而喻就是诽谤帕斯捷尔纳克是寄居在苏维埃红色政权内的异端分子。肖洛霍夫还攻击苏维埃另一个诺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当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国外发表,肖洛霍夫在一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公然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他指出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政者要对两位作家达尼哀尔和辛雅夫斯基(笔名阿尔夏克、杰尔茨)进行公开审判,理由是他们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了作品。这次公开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62位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信。许多人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而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并且直言不讳地干脆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肖洛霍夫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 对肖洛霍夫如此公开的卖身投靠,以至84岁的着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儿,诗人利季娅愤然写信给肖洛霍夫说:“您和我们大家都同样清楚地知道,俄国诗人始终是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的。您的发言把您置身于俄国传统之外。可惜我们不能惩罚您;不过您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了,罚您多年来创作力枯竭。” 国外的媒体甚至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出:对于这种违背诺贝尔设奖本意,迎合专制独裁政权的主流话语,丧失一个作家人格的获奖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诺贝尔奖金。 但是,从斯大林时代血雨腥风中的过来人,对肖洛霍夫给予一定的同情和理解。 杜勃罗留波夫曾为俄罗斯作家笔下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定义为“一群退出战斗的妥协者”。并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他们“否定了跟压迫着他们的环境做残酷斗争的必要”,“走进了一座郁苍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们攀援上树原本是想寻找一条新路,但上树之后,“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顾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轨迹,为俄罗斯文学史活生生勾勒出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是最好的鉴别。从帕斯捷尔纳克和肖洛霍夫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同经历和命运中,我们感悟到什么是一个作家应该持守的人格立场和道德底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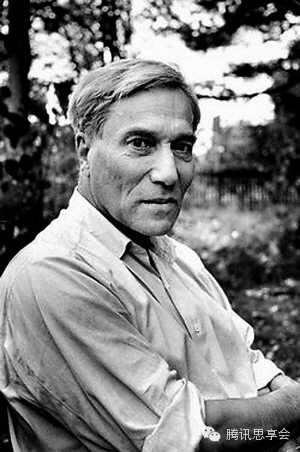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41:00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