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艺术大师保罗·克利的幼年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右起:克利、克利的舅舅[Ernst Frick]、克利的姐姐[Mathilde Klee] 伯尔尼 1886 保罗·克利( Paul Klee,1879—1940),20世纪最具诗意与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之一。出生于瑞士,父亲为德裔,母亲为法国与瑞士混血后裔。父母均是音乐家,唯一的姐姐早他三年出生。7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岁获高中文凭,前往慕尼黑习画;21岁正式进入美术学院学习雕刻与雕塑。1920—1930年执教包豪斯学院。1940年6月29日病逝。他一生致力于抽象与非具象表现的探究,由观念描述转入视觉,从人物转入大自然与历史,乃至于纯艺术的追求;他借由象征来传达艺术理念,为后世画家树立了一个崭新的典范。 童年时代的回忆:伯尔尼[1880年至1895年] 我这童年时代的回忆录开始前,应该加上一段小序。1879年12月18日,我出生于伯尔尼附近慕尼黑布赫湖的校舍里。当正在霍夫维尔师范学院教音乐的父亲获准永久居留伯尔尼之时,我才几个月大。起初,我们住在一条名叫亚勃格尔,听说又穷又不起眼的巷子里;不久搬到又大又阔气的合勤尔街32号,我不记得这层房子的情形了,只知下一个家是26号,从3岁到10岁。然后迁至基亨费尔德[Kirchenfeld]的玛利安街8号,消度我童年时代较不幼稚的晚期。中学的最后几年,我们住在水果山麓上的祖传庄园。我很早就培养出某种审美能力;在我仍着裙子的年纪便须穿上内衣,内衣长得露出了滚着红边的灰色法兰绒。门铃一响,总要躲起来,免得客人瞧见我这副模样。[2―3岁]大人谈话时,我设法从那快速流动的句子中抓住单词。没意义而无止境的句子,就像一种外国语言。[2―3岁] 很小的时候,外祖母教我用蜡笔画图。她使用一种特别柔软的卫生纸,所谓的丝纸吧!她吃苹果时,并不咬上一口,或者一片片放入嘴里;而是用削鹅毛笔的小刀把苹果刮擦成浆状。酸酸的气息,间歇由她胃中升起。[3―4岁] 保罗·克利伯尔尼1892 长久以来,我深深信任父亲,把他的话当做纯粹真理。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老人家的揶揄。有一次我独自沉醉于一些好玩的哑剧里,突来一声逗笑的“扑哧”,打断了我的兴头,真叫人痛心。后来回忆时,偶尔也可以听到此种“扑哧”。 我以前画过的邪恶神灵,忽然有了真实的形象。我奔向母亲要求保护,抱怨小妖魔在窗口窥视。[4岁] 我不相信上帝,别的小男孩经常像鹦鹉般地说:“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们。”我认为这是一种差劲的信仰。一天,有位很老的祖母在我们那兵营似的公寓房子里去世,小男孩们纷纷宣称她现在是个天使了:我压根儿不信。[5岁] 外祖母的尸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经觉察不出她生前的面貌了,我们不准靠近。而玛西达阿姨的泪水像条静静的小溪流着。当我经过通向医院地下室停尸间的门时不禁要打冷战。我听说死人会吓骇我们;可是,我想流泪还是专为大人保留的习俗吧![5岁] 狂歌 1889 克利10 岁时候的作品 我时常戏弄一个小女孩,她并不漂亮,还戴着夹木以矫正弯曲的双腿。我把她全家人,尤其是她母亲,看成拙劣的人。我假装是个好男孩,出现在高贵的宫廷上,请求那位母亲准许我带她的小可爱去散步。我们两人手拉手和平地走了一段路之后,多半是到了马铃薯开花、金甲虫嗡嗡飞的近郊田野,便开始成单行前进。时机一到,我把被我保护的人轻轻一推,可怜的小东西倒下去了,然后泪汪汪的我把她带回她妈妈身边,以天真的口吻解释:“她摔跤了。”这个玩笑我开上好几天,恩格太太不曾怀疑什么。我应该重新判断这个人。[5或6岁] 在我想象中,成人世界里的一切自然都不一样。母亲上歌剧院的第二天,她称赞那男高音,我心中勾勒出这么一幅图:没有扮相,也没有戏服[这只是小孩的玩意儿];而是一个身穿燕尾服,手执乐谱的男人,顶多再来一点小布景,或许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6―7岁] 我常到全瑞士最胖的男人——开餐馆的胖舅舅家里看看报纸,画画图。一个客人看我画马和马车,完成后他说:“你知道你忘了什么东西吗?”我心想他指的可能是马的某一器官,便以倔犟的沉默来回答这位故意为难我的人。最后他说了出来:“是车轭呢!”[6―7岁] 胖舅舅善于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有一次他学猫叫来愚弄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搜遍全餐馆要找那只猫,直到后来舅父发出喇叭似的噪声,想结束这出恶作剧,可是男孩铭记在心头,半出于愚笨半出于捣鬼地说:“讨厌的小猫咪咪叫。”我听了颇为反感,我才不会在高尚的社交场合使用这样的言辞![7―8岁] 无题/ 家与阶梯/ 马车 素描 14.9×18.3cm 1890 人家告诉我裁缝师是坐在桌子上的,我深以为这是个不伤大雅的小谎。但当我真碰到这么一个家伙坐在桌子上时,惊讶的程度仿佛瞥见幻象变成肉身。[7岁] 上学的第二年,我已对赫密妮[坐在我隔壁的女孩]怀藏特殊的感情。犹记得在教室内的一刻,我们一起坐在书桌上,脚摆在长凳上,注视着挂在后头墙上的海报画。她牵动鼻孔不断微笑的样子,傻傻的,心不在焉地从裙边拾起玻璃珠子。我向左边匆匆看了几眼,觉得在这世界里好不安然自在。[7岁] 有很久一段时日,我几乎无中断地忠实对待卡朱黎;甚而今日我仍可发誓她是一位美丽的小淑女。那是一股强烈而秘密的爱情。每当我们不期而遇之时,我的心不禁颤抖,可是依然简短而羞怯地问候对方;在别人目击之下,我们的举止恍如互不相识。有一次见面,她穿一件淡红色的衣服,头上戴一顶红色的大帽子。另一次她沿着吉辛费德桥倒退走,差点就跟我撞个满怀,当时她穿的是深紫蓝色的短衣,戴的是小帽子,发辫丰厚而松垂。她父亲是德裔的瑞士人,母亲来自日内瓦;家里有5个姐妹,一个比一个漂亮。[7―12岁] 我从花园篱笆的隙缝偷了一个大丽花的球根,移植到我自己的迷你花园中。我期待它长出一些好看的叶子,也许还会有一朵友善的花,然而却变成满片暗红色之花的一大丛东西。突然在我心底唤生某种恐惧感,我一再犹豫想把它送给别人,以放弃这不安的占有。[8岁] 套勃河上的罗腾堡 1896 年12 月 胖舅舅餐馆里的桌子罩以光亮的大理石片,这些桌面像是坚硬的石头构建的迷宫。你可在其纠缠的线条间,挑出怪异的人形图案,然后拿铅笔将之捕捉下来。我着迷于此项消遣,我喜爱奇异事物的生性油然流露。[9岁] 我清晰记得在麻利[Marly]二度逗留的情景。这奇怪的小镇位于比亚瑞河[Aare]更绿的一条小河河畔,街道上没有夹立的拱廊,据说内藏跳蚤的马车行过可自由开闭的吊桥。好一个天主教意味的地区!开寄宿舍的柯绫姐妹操着法兰西方言,肌肉发达的那位在指挥一切,温柔的尤琴待在厨房。那儿的苍蝇、饲养家禽的院子、宰杀这些动物的景象!松鼠在轮圈里转动。楼下的水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午后的户外咖啡座。四海为家的孩子,有些来自亚历山大港的,早已搭乘大如房子的船只在海上旅行过,那个粗野而肥胖的男孩来自俄罗斯。附近乡村中的散步。小小的摇摆的人行桥。大人们在桥上害怕的样子。吓人的雷雨。好多保龄球道。在溪中游泳。高高的芦苇。伤心道别这个乐园。 第三次的逗留肯定并强化了上次所拾掇的印象。胖胖的快活的年轻传教师跟我们玩占椅子的游戏。[约6―8岁] 我首次去观赏歌剧,是在10岁的时候,那时正在上演《吟游诗人》。剧中人物备受哀苦、不曾宁静、难得欢悦,震撼我心。但我随即对此悲伤格调感到亲切,开始喜爱那流浪的蕾诺拉;当她的双手在唇际狂乱摸弄之时,我自以为那是一种咬牙切齿的姿势,我甚至看到几只龅牙闪烁生辉。《圣经》里惯有扯破衣服的角色,为什么拉扯牙齿不能算是一种美丽动人的悲愤表情呢?[10岁] 倒霉,一些黄色素描落入我母亲手中;其中一张画的是一个抱小孩的女人,另一张极为袒露。母亲站在道德立场来责骂我,太不公平了。那袒露的女人是我看了一场芭蕾舞表演后的成果,一个颇丰满的小精灵弯下腰去采草莓,你可以凝视挟缩在隆突山丘间的深谷,我怕得要命。[11―12岁] 我手边有一册威尔布兰特[1]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来自金星的访客》一文我读得津津有味;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问题人物对我这年纪无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此一观点,“问题”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不懂的东西,无疑以后会搞清楚吧,至少可以满足一部分好奇心吧。 [1]威尔布兰特[Adolf von
Wilbrandt,1837―1911]德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来源:《克利的日记》 作者: (德)保罗·克利 译者: 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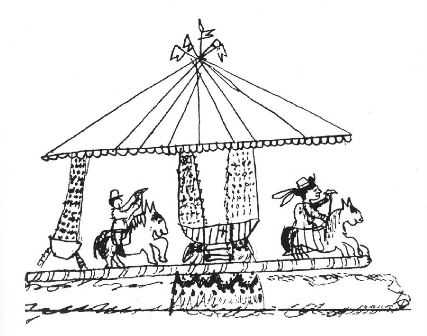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8:1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