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精英办公桌杀人者
 |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 簡體 傳統 |
撰文: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翻译:严春松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一书中首次揭露:为何残忍的种族清洗是近代产物。无论是那些最骇人听闻的事件——殖民主义的种族灭绝、亚美尼亚、纳粹大屠杀、柬埔寨、南斯拉夫、卢旺达,还是那些残酷程度稍轻的案例——近代早期的欧洲、当代印度、印度尼西亚,它们都是“民主的阴暗面”。 当同一片领土上,两个对立的种族民族主义组织都声称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时,危险产生了;当弱势的一方由于外部的支援而不愿屈服、选择战斗,或者强势的一方认为自己能够骤然展开锐不可当的武力行动时,冲突便升级了……行动升级并不只是“邪恶的精英”或者“未开化的民族”的杰作,它同样产生于领袖、激进分子以及种族民族主义的“核心拥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曼的解读聚焦于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关系,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种族清洗的源头及升级过程,有助于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以下文字节选自该书第九章:“纳粹III:种族灭绝事业”。 事业路线之一:精英办公桌杀人者 绝大多数帝国中央保安局成员不习惯于暴力。他们是同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太年轻而未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帆风顺,受过高等教育,三分之二有大学学位,三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在大学时就曾是纳粹或激进右翼分子,1933年前加入纳粹。到30年代中期他们准备按照纳粹种族—国家学说重新改造世界。他们知道需要采取行动,当时机到来时他们极少有人退缩(赫尔伯特,2000:26—27;怀尔德特,2002)。 阿道夫·艾希曼是以善于解决问题而着称的人。他监督将纳粹、军队及平民管理机构与死亡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驱逐手段。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讯时,精神病专家说他是模范丈夫——“在考查过他之后,我觉得他比我更正常”,有个人这样说。他出生在莱茵兰德,八岁时母亲去世,全家搬到了奥地利。他在初中读书期间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里做销售员,表现都较一般。1932年他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当时26岁;1934年,在那段非法时期,他听从朋友卡滕布伦纳的建议加入了党卫军。他当时对加入党卫军给出的理由是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和大规模失业,但是事业受挫其实也是原因。1934年他经训练成为达豪集中营的一名中士,次年进入党卫队保安处犹太部,在此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专家。他把自己描述为“不感情用事和客观的”人。对阿伦特(1965)来说,他是“平庸之恶”的缩影(一个她后来开始后悔使用的词)。她觉得从道义上他“从未认识到他是在做什么”。这不是真的。艾希曼反犹非常坚决,他对犹太问题以及它的多种解决方案的专业业务知识已使得他做好了接受任何考验的准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1978:105)回想起他们战时的谈话: 即使是在我们俩独处,随意喝着什么,能充分放开情怀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他老在思忖如何把每一个他能逮住的犹太人都灭掉。我们必须弃绝怜悯,不带任何感情,尽可能快地完成这种根除。任何妥协,哪怕是最微小的,也必定将在以后使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赫斯等,1987:105) 他一次次告诉朋友,犹太人除了做劳工别无任何价值——而其中仅20%—25%的人能从事艰苦工作。迪特尔·威斯里舍尼(见后)说: 他不是不道德,他是根本没有是非,一副彻底的冷漠无情的样子。1945年2月他对我说——其时我们正在谈论关于输了245战争之后我们的命运:“当我跃入坟墓时我会哈哈大笑,就因为我杀掉了500万个犹太人时的那种感受。那能给我很大的满足和自得。”(战犯审判,1946:第8卷) “冰冷”(Ice cold)意味着冷酷无情,不是置身事外。只有他在法庭上的技巧是平庸的,老是想开脱责任,不承认他发出过的命令。但他本人经常采取主动。他反对驱逐塞尔维亚犹太人,一位同事记在议事录上,“艾希曼提议开枪射击”。1942年艾希曼反对把犹太人从匈牙利驱逐出去。他说,最好,等到7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能够一次性全处理掉。他的建议两次都被采纳。这不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官僚政治:它是不固定的,允许官员往激进的方向进行创新。艾希曼的邪恶既不是不加思考,也不是平庸,而是革新性的、冷酷无情的和意识形态的(洛索威克持一致看法,2000)。 我跟踪了往单一国家方向驱逐的行动过程。与艾希曼紧密合作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是两个有特殊背景的纳粹。外交部高级代表叫艾德蒙德·费森迈耶,一个来自下法兰柯尼亚(巴伐利亚州)的天主教徒。他曾是经济学讲师和成功的商人。作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1932年他投向纳粹党。从1933起,党卫军为他的外交生涯提供资助。他晋升为党卫军中的准将,在说服匈牙利政府支持大规模驱逐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写道:“犹太人是头号敌人;110万的犹太人,意义等同于数量有如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员的阴谋家。”党卫军保安处头号人物是奥托·温克尔曼中将,出生于霍尔茨维格—霍尔斯坦,一名城市官员的儿子。在还是学生时,他就参加了1923年在鲁尔地区对法国人的战斗,结果被关押。作为一名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在1932年28岁时他转向纳粹党。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在“犹太人对外移民”局匈牙利司工作。他出生于1911年,22岁加入纳粹党,23岁加入党卫军和党卫队保安处。 他们的员工——如士兵伯格、格雷尔、亨谢、克鲁迈、诺瓦克和斯伯林茨——是一直伴随自由军团或具有在德国或奥地利的巷战经历的老的或年轻纳粹(克鲁迈是个例外,仅到30年代中期才参加民族主义的继而纳粹的前线组织)。匈牙利驱逐行动被有意交付给可靠的人安排处理——因为他们全部在被占领国。这些是意识形态纳粹,有事业前程是他们的奖赏。就像对集中营中的上层精英一样,他们的目的与效率更容易从一个系统性的严格的意识形态中产生:追求“道德”清洗。这最终意味着不放过一个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正如洛索威克(2000:8)所说,这是一个执行世界历史任务的精英群体,意识形态上的效率专家,不是平庸的官僚。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直至最后一滴血。 被占领领土的长官和警长监督着在实地进行的杀戮。他们是凶狠的纳粹,经常在政变发生前已富于巷战经验。与办公桌杀手不同,他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杀人。他们慷慨激昂地宣扬一套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我们是优越民族,我们当中最低级的德国人也246比当地人口在种族上和在生物学上珍贵1000倍。”厄恩斯特·科克来自鲁尔,是一名铁路职员,因早期从事政治活动而被解雇。在20年代末期做了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之后,他成了乌克兰的帝国专员。“我对犹太人一无所求,除了让他们消失。”来自巴登的汉斯·弗兰克说。他是一名自由军团老兵,一名纳粹党的律师,是当时帝国的司法部长和波兰的最高行政长官。约瑟夫·伯克尔态度较为犹豫。他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是一名手工业者的儿子,一名来自自由军团的老兵,做过老师,在20年代末期成为一名党内官员。他是一名保守的、热爱秩序的纳粹。1938年他是维也纳的地方长官,在此他试图抑制针对犹太人的野蛮抢劫与暴力。但当被告知希特勒支持此项行动时,他改变了观念。他开始为元首工作。 东部警察指挥官中的老前辈是冯·丹姆·埃里克·巴赫-齐烈夫斯基,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容克军事家庭。他参加了“一战”,然后服役于自由军团和魏玛军队。受希特勒影响,他辞去了委任,1930年加入了纳粹党,时年31岁,次年加入党卫军。作为一名12年的纳粹帝国议会代表,罗姆清洗及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部队的指挥官,他是希特勒的爱将,因“将共产党反动派彻底击垮”受到希特勒的赞扬。在一次特别行动队完成任务之后他吹嘘说:“爱沙尼亚没剩下一个犹太人。”后来他又清洗了华沙犹太人居住区。 但他也有疑虑。1941年希姆莱去观看一次特别行动队清洗行动。因明显紧张,他往后退缩,在每颗子弹打出的时候避开希姆莱的注视。射击结束后,巴赫-齐烈夫斯基袒露了自己忐忑的心情,说: 元首,那些只是一百次(杀戮)……看看这个突击队中的士兵的眼睛,他们是怎样地在深深发抖!这些人的余生算是结束了。我们在这里训练什么样的跟随者?要么是神经病,要么是野蛮人! 极少有高级纳粹在经历杀戮时没有道德上的犹疑。大多数人试图将他们自己放在一个据称是更高的道德目的之下。伯恩(1986)将这归于严格的军国主义熏陶、战争经验、感情上往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向,以及对希特勒的极端服从。但是服从希特勒给了他们一种理想主义意识,个人的感情已服从于共同的事业。这类扭曲的理想主义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施害人当中很普遍。当其他动机都不起作用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力量帮助了施害人将任务坚持到底。 非纳粹机构也参加了合谋。没有文职部门,几乎什么事也完成不了。极少有文职官员有任何暴力或狂热主义历史。在外交部,布朗宁(1978)指出了两类参加合谋的官员。第一类是1933年之前以及加入外交部之前具有知识背景的纳粹成员。路德出生于柏林,一个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参加战争之后,他开了一家家具248进出口公司。1932年3月37岁时他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但这时他已经认识了许多纳粹,还是里宾特洛甫的朋友。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纳粹柏林城市市政会委员。布朗宁称他是“一个与道德无关的权力技师”,但这不是很恰当。他在成为职业外交官之前是职业纳粹,只是在1936年进入外交部,然后很快得到晋升。 布朗宁的第二类人员是单一的野心家或追名逐利之辈,在政变后加入纳粹党,属于见风使舵的纳粹。他们包括了像奥托·冯·诺伊拉特那样的贵族保守派外交官和像弗朗兹·拉德梅克那样向上流动的男人,后者是一名来自梅克伦堡的铁路工程师的儿子,到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凭自己艰苦努力才进入犹太人事务部工作。布朗宁认为这些人比艾希曼更好地展现了平庸之恶。然而绝大多数是来自军事和文职官员背景,而整个部门中渗透了反犹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拉德梅克坚信科学的种族主义——这是他能帮助起草马达加斯加计划和最后解决方案的主要资格。在我的样本中,几乎所有的文职官员——相较于很少的商人——都被吸收成为纳粹。但是他们的纳粹意识形态极少是用赤裸裸的言词表达的,更少采用暴力方式。相反,它在他们所在的比较威权主义的文职部门中的职业经验中获得了反响。 1942年在万塞召开的臭名昭着的副部长级会议奠定了在党卫军与文职部门之间执行最后解决方案所需要的合作基础。纳粹领袖原以为文职部门会有不同意见,然而一切进行顺利。这很可能是因为除了克里青格(一个来自波兰的德裔)之外的所有参与者都是老纳粹。绝大部分讨论与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异族通婚的技术问题有关。一个半小时之后会议结束,继而是喝茶休息,然后是午饭时间。最后解决方案的消息通过各个部门向外扩散,没有引起很大骚动(希尔伯格,1978:264—265)。一味追名逐利的做法现在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高级官员担心他们会失去影响,需要他们所在的部门设计杀戮方案,而中层官员可以通过去到处涌现的犹太人司工作来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财政局制定被驱逐者财产清单,然后把它们交给税务局,劳动局收集工作手册,房产局处理空置房屋,而国家铁路部门修建通往集中营的铁路并运送囚徒。 实际上这些人中谁也没有杀人,也很少有过暴力历史。布朗宁(1978)说他们将“一种去个性化的行政操作模式”、“一个政府阶层的组织性成就”和“意识形态的灌输”结合在了一起。但是他们以前的右翼意识形态思想相对较容易地变成了一种国家主权论的纳粹主义,给予他们的追名逐利做法以一种原则性的色彩。官僚政治是远离了杀戮的文职部门领域进行种族灭绝的手段,而纳粹意识形态的响应给出了目的。继续向东,两者的结合显得更加地迫不及待。文职官员知道他们的249意识形态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的一味追逐名利也更加赤裸裸。被派往波兰和俄国工作的差使不受欢迎,并且人们经常是因为失业,甚至有犯罪活动才去的。穆夏尔(1999)认为这些官员贪污腐败,公开地显露种族主义倾向,试图通过谋杀的热情来救赎他们自己,恢复他们的事业前程。 产业界的情况不一样。我在《法西斯主义者》中强调资本与劳动力都不属于纳粹核心拥护者,很少商人是意识形态纳粹,尽管许多人在1933年之后赶浪潮加入了纳粹。他们开办奴隶劳力工厂,但不是为了利润。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同谋,因为随着战争的进程,劳动短缺成为燃眉之急。有纳粹关系的产业主义者,如波西亚,通过游说将囚徒作为劳力——先是西欧人,然后是斯拉夫人,最后是犹太人。到1942年年末,三分之一的德国劳动力是奴隶。他们的待遇相差很大。一些犹太人受到很好对待,比其他工厂里的法国或荷兰劳力的待遇要好。然而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的经理吩咐替换患了病的劳动者,同时心里知道他们之后会被杀掉,而管理者定期地进入集中营挑选劳动力,斯特雷德说(1999)。 甚至在为数不多的被控告犯有战争罪的产业主义者和管理者当中也极少有人在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古斯塔夫·克鲁普“榨干了”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和犹太奴隶劳动力,所以他被免除了继承税,但是他从未加入纳粹党。库尔特·施罗德和弗里德里克·弗利克从1932年起曾帮助资助了该党,然而弗利克给予其他右翼党更多,并只到1937年才加入纳粹党。施罗德1933年加入纳粹党。甚至是来自波兰的失去领土上的“无耻和残忍”的埃里克·迪特里希——他为他的企业从当地城市贫民窟招收工人,同时将孱弱者交给盖世太保枪决——也是在1935年左右才入党。产业主义者和金融家也采取赢利的政府的经济立场,经常与党卫军密切合作。银行经理汉斯·菲施博克是德奥合作后的奥地利内阁成员,然后去帮助管理荷兰经济。他是右派,尽管只到1940年才成为一名正式纳粹,此时他得到了党卫军上尉的名誉军衔。在德国资本家中我们距真正的平庸最近——大规模屠杀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某种已被制度化和具有合理性的事物的副产品:从最小的成本中榨取最大的利润。因为自由劳力供应短缺,价格昂贵,资本家乐得使用奴隶。当然,资本家、管理者甚至工头不是一定要去杀人。他们把奴隶移交给党卫军,然后就试图把他们全忘掉。他们主要是杀戮行为的物质主义同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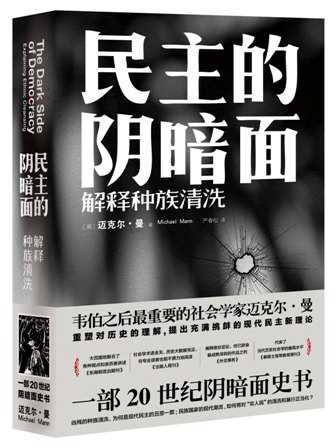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6:3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