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于一爽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作者自拍效果图 《同学聚会》讲的是一个没什么出息的中年男人"我"参加大学聚会碰见了当年的女同学,相互说得最多的话是"你胖了"、"你也胖了"。之后又见了一次,女同学在精神上受制于人已经难见当年面貌,只能借着酒劲儿拼命回忆,而"我"已经不想搞她,于是匆忙告别,去找了小姐。 我不相信也得相信,在我们见面之后不到一年,余虹就死了。她跟一男的在京津高速上钻到一辆大解放里头去了,听说脑袋被削掉了一半儿。当老牛跟我说余虹脑袋削了一半儿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一阵恶心,她那个脑袋呀--我一点儿没因为旧日感情而有丝毫悲伤,我倒想起那次同学聚会。但这并不能缓解我的恶心。 我叫刘明,属鼠的。一般老喜欢跟人说我属耗子。1972年出生的,眼下,我就快40了。如果2012只是开个玩笑的话,我倒真觉得失望,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的2013我能有什么改头换面的地方。我在一家影视公司做文学总监。听听,听着还真不错是吧,可是这年头,总监比耗子都多,何况我们公司,大老板喜欢女演员,小老板成天忙着给大老板找女演员。谁想做事儿啊?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也能混得挺好。谁要看见我现在这副德行,真想象不到我当年也是中戏的。往前倒退十几年,中戏出来的可不像现在如过江之鲫,那会儿都特有理想,如果想到日后终会一事无成恐怕倒会活得老实点儿。 大概10个月前,也就是去年秋天,我接到老牛电话,说,聚聚?我开始没听明白,他又说,聚聚?老牛当年和我一班,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快2012了,咱们老同学再不见就见不着了。 我当时挂了手机就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没想到,我同学都这么庸俗了,聚聚就聚聚,提什么2012,又不是90后,真死了还有点儿可惜, 毕业十几年,我正经联系的没几个,跟老牛有时候打打电话,他在 社会上小有名气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剧组骚扰小姑娘上了新闻头条。要我 说,真得怪这土鳖运气不好,那会儿是90年代,坏风气刚刚抬头。 虽然啐了口唾沫,我还是同意去了。一方面闲着也闲着,二方面我 有点儿想重温旧日情怀。这可真够恶心的。 我们的同学聚会定在了三里屯的"一坐一望",去了之后我才知道, 其实也不是老牛提议的。说来也是,老牛混得也不怎么样,他大概是想 拉一个更不怎么样的垫底儿。 这么一想,我就舒服多了,也不像刚迈进门槛时候那么紧张了,自 我羞辱真叫人觉得轻松。 1994年我刚毕业,还是个挺利落的瘦子,现在肚子大得打炮儿都 得先挪后头去。我媳妇儿跟我结婚十几年,对我的长相先是从看不起到 压根儿就不看。有时候我光着个膀子在屋里转悠,她就跟没这个人似的, 转悠晕了她来上一句:"瞧瞧,瞧瞧你这肚子!" 我每次都说:"是,我哪儿像一搞文艺创作的啊,说我是刘屠户还差不多。"那天进了包间,猛一看我真以为进错屋子了。老牛挺大声来了一句:"刘明,别找了,这,这来!"我才恍过神,这一屋子妇女还有大叔。岁月是把杀猪刀。 后来我找老牛坐着。又跟几个人打招呼。应该是老年痴呆提前了, 张弛跟我说他叫张弛,我思绪万千半天,张弛谁啊?我们班的?艾丹也 说:"嘿!刘明,你也不理我。"我哼哼哼!心想,艾丹?咱认识?接着又 哼哼哼,最后直接喝酒。我真跟你们这种混蛋做过同学,不能吧?当我这 么想的时候,我总是摸摸自己滚圆的肚子,我也不是当年的我了,可我 还是不愿意那么去想。于是又喝酒,我一个劲儿跟在座的,少说得有十 几个人吧,干杯,一杯接一杯,压根儿就没吃上一口。还跟几个人递了名片,有几个一看我就笑了,嘿,跟我一样,总监,咱比耗子都多。哈哈哈,越到后来越晕,高兴得不得了。其实,也不是高兴,可我总不能不高兴吧。就这么硬撑着。真他妈没劲透了。印象中,我还摸了一姑娘的手,也不是姑娘,妇女了,就坐在我左边的左边。我右边是老牛,左边是谁来着,忘了。左边的左边说自己叫余虹,她说你还记得我吗?她说我喝多了。我说那咱俩喝了吗?因为有时候见面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摸了一把她的手。 我说:"余虹啊,你就是余虹啊,你怎么胖了?" 她说:"你也胖了。" 我说:"我胖得不成样子了。" 她说:"可仔细看还是你。" 我说:"是吗?那你再仔细看看。" 后来我们就什么都没再说。因为我左边的一直哼哼,说别胡来啊,你妈的,你把余虹都忘了。我说老同学了,叙旧,你们别闹。其实我还想说我内心无限伤感,可是胖子好像不能伤感,尤其像我这种胖子,猛一看以为混得特好,伤感,一准儿以为是闲得蛋疼。于是我松开余虹的手,正好憋得尿急,我去了卫生间。跨过几个人的时候,我还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当然我也知道,这个世界光拍拍肩膀显然是不够的。 从卫生间回来之后,我稍微清醒了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我想起余虹是谁了。一方面是我们做过同学,另一方面是,她是我追过的挺多女孩儿中的一个。至于其他那些女孩儿都哪儿去了,我想她们跟我再没关系。 于是我回到座位之后,跟我左边的换了位置。就算我不换,我也能挨着余虹,局已经乱了,有人喝得七仰八歪,一个劲儿地回忆往事。老牛说当年身体可真好,夜里玩儿牌,早晨操场没人,正好踢球,踢到十点来钟回宿舍睡觉,起床就去喝酒。着另外一个老女人。 我喝了几口可乐漱漱嘴,坐到余虹的左边儿去了。当我咕咚咕咚喝可乐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当年。余虹好像酒量不错,她两颊红扑扑的,一举一动都看着挺清醒,她正往嘴里扒拉一碗米线。我点了根儿中南海看着,我喜欢看女人大口吃东西了,我觉得她们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做爱。当然,我现在想这些也有点儿没必要,别说做爱,趁我尚还清醒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跟余虹好像只是拉过手。 "来点儿?"余虹指着碗跟我说。她一定觉得我喝多了,她想让我吃点儿。我把烟掐了,用她的筷子胡噜了两口。然后放下筷子又点了根儿烟。我说:"这一晃,我们得多少年没见了?" 四周乱哄哄的,我的问题怎么听怎么像个傻B。余虹一笑,当她一笑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有20岁的模样,或者她 压根儿就没有20岁的模样,因为我只见过当年所以一直那么希望。我觉得我不讨厌她。除了我老婆之外的女人,我都不讨厌。余虹说:"给我来根儿。"我给她点了一根儿,我还问她:"中南海行吗,点儿八?"我觉得女 人都得抽那种细细的,这样才对得起生活。余虹说:"少来。"她这么说的时候,红扑扑的两颊上长出一个小酒窝。少来,呵呵, 可爱极了。 "你好吗?"她问我。 没等我说,她就又说:"可是和当年想的不一样。" 我说:"什么?" 她说:"很多事情。" 我说:"干吗伤感啊?" 她说:"不啊。" 我问她生活得好吗。她说,还不错,可是干的事儿和当年学的没一点儿关系。其实我压根儿不关心她干什么,别说干什么,她不干什么和我有关 系吗。我是想问,你结婚了吗?余虹听出了这个意思,说,我结婚了。接着她哈哈大笑,说就那么回事儿,挺好的,也挺有钱的。我说,那就好那就好,结婚就好,有钱比什么都强。我又说,我也 结婚了,不过唯一的区别是,她还有个孩子,她说是姑娘,快10岁了。我又一个劲儿地说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还没有孩子那你的现状还不是最坏。后来余虹说要去卫生间,我说,走,一块儿。当我们俩一块儿往外走的时候,老牛起哄,好像他掉了颗门牙似的。 我说马上回马上回。光天化日之下我还能干什么啊我,关键是我也不想,当年都没有的事儿现在就更不想有了。但是从卫生间回来之后,我跟余虹又在过道里多站了一会儿,她说外面清净。我说都好都好。 在过道站着的时候,我们时不时就得侧过身子给路人腾地儿,有时转得有点儿猛,余虹就会贴我肚子上,不过马上就又分开了。两人东扯西扯也没什么可说的,女人最大的话题是孩子,可是我对这个想都没想过。她问我,你就没想过要一个。我说我没想过,我又说我真没想过。 当年我发誓娶我媳妇儿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爱她,她当年也想生,我总说等等等等,好在她现在生不了了。要是生了,医生说,就得等着变成一大胖子,挺难恢复那种。她要真成了大胖子,我们俩就更没性生活了。当然这些都是我的心理活动,我可没跟余虹说半句。 我只是说:"真快,可真快啊,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咱俩也老戳在过道儿。"不了,要早点儿回家,小孩儿等着呢,改天吧,改天去我家玩儿。 我说那好吧,她说你可一定来啊。我说来。她又说:"哦,对了,咱可连个电话都还没留呢,别回头一分开又是十几年。"我想,再过十几年,人肯定就聚不齐了。要是再过两个十几年,全一堆儿一堆儿的了。 后来她跟我说了手机号,我给她打了一个,她说:"那,先这么着。你再跟他们玩儿会吧。我走了。"我说:"行吧,再约。慢点儿。到时候电话。" 当我跟她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还能见面。 人总是得讲点儿礼貌不是吗? 余虹走了没几分钟,我就喝多了,我觉得没必要再保持体面,我跟张弛啊艾丹啊老牛啊的来了个大满贯,谁是谁我差一点儿就都想起来了。 回家的时候没有1点也有12点半了,我媳妇儿赠了我个白眼球就上床睡觉去了。我当时借着酒劲儿挺想做爱的,裤子都没脱就往她被窝儿里挤。我媳妇儿倒好,来了句:"你别强奸我。" "强奸,要强奸你还不是分分钟。"我这么说的时候,主要是在吹牛。接着,我就打起了呼噜。好像还被谁踹了几脚。我骂了"骚B"两字,很快就做起梦来。 我的一天总是在这种事情中结束。 我很生气她压根儿没问问我同学聚会的事儿,我虽不是什么金元宝可也不至于一钱不值。 不过我也就那么想想。因为第二天起床我媳妇儿还问我:"你昨儿骂谁啊,我骚吗?"我当时宿醉未醒,我说我没闻过。她使劲捶了我两拳,又问我:"头还疼吗?吃不吃阿司匹林?"我勉强点了点头。 那天之后很久,我的生活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平静。那种生活对我来说之所以平静,主要在于太过熟悉。我每天出去吃吃饭喝喝酒看看本子有时还见见北影中戏的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可真好,她们总让我觉 后来有一天,我正在家上微博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没有显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所有没有显示的号儿我都听听,我是怕错过什么机会,我媳妇儿老说我贼不走空。 "喂?刘明啊。"电话那头儿说。 "嗯……"我犹犹豫豫,我觉得电话线里头的声音也不是特别陌生。 "行了行了,一准儿把我忘了,我,余虹。" "什么啊,余虹啊。" * 幸亏她提醒了我,那天喝多了,压根儿没存谁的号儿。我又臭贫了两句,意思说这么多天了就等着她这电话呢。当我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点儿沮丧。我觉得何必呢。 余虹说:"要没事儿,明天来我家吧。"我说明天啊。我想了想(其实明天我没什么事儿,我哪天都没什么事儿,可我还是想了想。)接着她又说:"我孩子、丈夫也在,不然你叫你媳妇儿一块儿,随便吃个饭。其实那天还挺想跟你多聊会儿。" 我说:"是啊,那行吧。"后来她给我发了地址,真没想到我们住得这么近。至于我媳妇儿,我就从没带她出来吃过一顿饭。我还没想好明天跟余虹聊点儿什么。有什么可聊的呢?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 第二天晚上到了余虹家,果然没见到她丈夫孩子,可我还是问了一句。她说他们晚点儿回来,她说要不要出去吃,我说出去吃吧,想吃什么,得我请。她让我在客厅坐会儿,她去换身儿衣服。我说你忙你的,我转悠转悠。我说你家装修得不错啊(这肯定是我编的,他们家是老干部风格,我觉得傻透了。主要是我实在不知道说点儿什么)。余虹说:"你就编吧。" 她这么一说,我觉得都怪我没话找话,接着我又看了看她客厅里的结婚照。她本人可比照片上老了挺多,我说:"累吗?平时。"她"呵"了一声,好像这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走吧。" 鞋的女人,我很喜欢。我们出了门儿,我们去了一家广东馆子。 余虹点了几个菜,她说喝吗?我说都行。都行的意思就是喝,不然我们相视而坐实在尴尬得要命。广东馆子都喜欢在墙上挂个电视机,在我没有感觉喝多之前,我一直盯着看,各种新闻。余虹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这么多事情。可是我们还活着。" 活着。她竟然说了活着。我想她疯了。另外我真搞不明白她为什么把我叫出来喝酒。就像我说的,她是我追过的众多女孩儿之一,可也就是拉拉手。如果拼命叫我回忆的话,也许能想起来--当初,我们一起做了四 年同学,还有半年时间在一个剧组实习。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在大兴安岭弄一个戏,每天收工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儿吃饭喝酒聊天,聊到热情澎湃的时候,她总是拽着我的手,说是要为祖国四化做贡献……那会儿我还是个童男,有次在大兴安岭深处(听听,这可真够抒情的,也没准是我编的)我说,那咱俩好吧。 我都忘了余虹当时怎么说的了,她大概是说--好?后来我们又说这说那……不过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也不怎么想回忆。我真担心我无非是在 夸大当初那点儿好感。也许仅仅是人到中年生活了无新意总想重拾一点旧日时光。再或者说,搞一下,这容易得不得了。"刘明啊,"余虹说完"可我们还活着"之后好像还没完,又说,"你现在生活怎么样,幸福吗?"我说挺好的。其实同学聚会那天我就跟她说过,挺好的真挺好的。至于幸福吗,我早就没那么幼稚了。无论怎样我们都还活着。"吃菜,多吃点儿。"我跟她说。什么活着死了的,现在哪儿有人聊 总说:"刘明啊,我觉得你特有才,以后你要出名了可怎么办啊?"我当时总说:"出名!你骂我呢吧,这个时代只需要一般好的人,像我这种这么好的,哪儿能出名啊!"于是余虹总说:"吹牛。"当时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当年就是那么想的。 "还记得咱俩当初一块儿在剧组实习吗?"余虹夹了几筷子菜在盘子里捣来捣去说。"是啊。"我说,"那是什么戏来着?"后来我们就想了半天,我们把90年代中期的几个电视剧都回忆了一遍,可是好像没有一部是在大兴安岭拍的。再后来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以至于我们在一瞬间都不再相信,我是不是真的在大兴安岭深处跟她说过那咱俩好吧。 好吧,无论这是不是当真存在,借着酒劲儿,我们又聊了各自的生活。自从学校分开之后,大家就断了来往。余虹说怎么后来就没见啊。我呵呵一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见,应该是都忙,她叫我闭嘴。她说:"知道吗?你那会儿挺好的。"我说:"是吗?当初还没大肚子呢。" "唉。"余虹叹了口气。 我最不喜欢女人叹气,好像生活很值得惆怅似的。我一瞬间觉得女人都是一路货,我狂喝了几口,喝酒不就是为了喝多吗?我想到我老婆。我还是没想起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我觉得一切都不存在。 我跟余虹说:"我多喝点儿,你少喝点儿吧。" 因为她也不年轻了,不年轻的意思是--当我借着餐厅的灯光仔细看她的时候,她眼角的鱼尾纹儿也不比别的女人少。 余虹一个劲儿说没事儿高兴呗,后来又说你他妈别不喝啊。我说好好好。可是我真不知道,她威胁我干吗?还怪里怪气的。这就像当年她问我什么是好啊,气得我啊!当年我一个童男,你问我好不好,我没试 回到学校就跟一个低年级的女同学上床了。 我当时肯定是觉得好,特好,好极了,我当时应该是一点儿都不在乎余虹了。当时班上造谣说我跟余虹在大兴安岭谈恋爱的时候,我跟余虹都不怎么说话了。那些年,可真奇怪。不过很快彼此各奔东西。 "唉,别提这些了,现在我们不都挺好的吗?"我说。"好?是啊,唉,好吗?"余虹说,"刘明,怎么混了十几年,你把自己混成了一个胖子。"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瞅了一眼自己的肚子,我真不知道我的肚子 怎么招她惹她了。 "这话说得,跟我媳妇儿似的。"我嘀咕了一句。 "你媳妇?你提你媳妇儿干吗啊?那我再问你,你知道我丈夫哪儿去了吗?"余虹晕晕乎乎地说。 "啊?"我哼了一声,我知道她这会儿是真的喝多了,我说我哪儿知道你丈夫去哪儿了啊?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呢?"余虹说。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越到后来我越玩命儿喝啤酒,好像我觉得自己肚子还不够大一样,我真想把它喝成气球带我飘到房顶儿上去算了。余虹趴在桌子上,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我一个劲儿地点头。我越来越觉得她和我媳妇儿真没区别。她和很多40岁的女人都没区别,全搞不清楚自己丈夫去哪儿了。我甚至在想,如果我操一下她,她会不会停止喋喋不休。不过我只是那么一想,我肯定不会那么去做。可是我如果不去那么做一下,她为什么叫我来呢?她仅仅是想找个胖子一醉方休吗?我就这么等待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当我想不出怎么办的时候我都是这么办的。 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餐厅的人陆陆续续走了。我说:"余虹啊,你不回家看看孩子。" 她说你傻不傻啊你,她跟她爸去外地了。 我说哦。 沉默了半天之后我问:"那你怎么没去啊?" 她哼了一声,好像我是个完全不懂婚姻的傻B。 * "那,怎么着?"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后来我起身,结账,又像当年在大兴安岭一样,拉着余虹的手。她用手抓了抓头发,头发全给抓乱了,我很想给弄平,但是我没碰她。这绝不是因为我是什么正人君子,只是我闻着她一嘴酒气,我突然觉得不必了。 余虹屁股紧紧贴着椅子,看不出有要走的意思。我说:"关门了,换地儿吧。"我这么说纯粹是为了哄她,哄她回家,然后我也回家。我知道这个晚上搞砸了。有时候真应该相信那句话--其实还是不见最好。我拉着她的手使劲把她拽起来的时候,她嘴里又念叨我的名字。可是她都没睁开眼睛看一下,如果发现刘明早就是个胖子的时候,她一定 觉得没意思透了。当我把她拽到门口的时候,余虹说:"包。"她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让她靠门框上等着,我重新跑到二楼去 把她的包拿下来。这点上,她和我媳妇儿真是一路货,她们那包好像都是个什么牌子,我也不懂,我反正知道:贵的就是好的。女人想要的都是对的,我从不跟女人争论这些,这主要是因为我能给她们的不多。 当我重新跑到楼下的时候,气喘吁吁,余虹自己已经拦了一辆车坐在后面,打着双闪,她这是也想让我坐进去吗?然后呢?我想了一下。我打开车门,她的头靠在椅背上,头发把眼睛遮住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醒着,我欠着身子把包放她腿上,又使劲敲了两下叫她拿好。她"嗯"了一声,她把挡住眼睛的头发别在耳后说:"刘明啊,我喝多了,对不起。" 我说:"哪儿啊,你一人能回去吗?" 其实我这么问就已经不想送她回去了,否则我会跳上车什么都不说。或者直接紧紧抱着她。可是我不想,现在不想,趁着酒劲儿也不想。怎么说呢?要说的话就太残酷了,真的,太老了,余虹太老了,那次同学聚会的惊喜也很快被这种相对而坐的细节取代,我们唯一愿意回忆的只是在大兴安岭的年轻岁月。 余虹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儿,她都长了这么多鱼尾纹了她当然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刘明啊,刘明,我希望我们还能见。"她说,"你快点儿回去吧,不早了,下次我请你,本来说好我请你的。" 后来我关上车门,夜晚的出租车总是开得挺快。在街口的红绿灯停了一下之后,一切都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也马上拦了一辆,司机问去哪儿,我说丹提。我没有回家,我还是去了酒吧。在丹提门口的树坑里,我解开腰带撒了一泡尿。尿了挺长时间,我甚至觉得有点儿虚脱,后来我紧紧抱着一棵树,我去找了小姐。 那次之后,我和余虹没再见过,隔了一个春节,她给我发了短信,弄得我们挺熟似的。她说常联系,我说没问题。我还给她发了个笑话。再后来就是老牛跟我说余虹死了,车祸,车上还一男的,也死了,好像不是她丈夫。 这可真够突然的。我当时有点儿不相信,因为不愿意相信,我说:"余虹?哪个余虹?咱班那个?" 老牛说:"×!你行不行啊?余虹,余虹啊,你初恋!" 我没再说话,如果时间往回算的话,大概是的。当时班上只有两个同学被选去剧组,大兴安岭深处,他们都说我跟余虹是一对儿。余虹是那会儿班上最可爱的,没事儿就顶着俩酒窝"嘎嘎嘎"笑,我当时老想着找个机会问问她--你笑什么笑啊? 于一爽的小说 by 张定浩 "我喜欢她小说里一种轻的东西。"在于一爽的小说里,那个名字总是叫做余虹的女主人公在欢爱之余偶尔也会谈论起文学。 "松弛。"那个名字总是叫做刘明的男主人公准确地回应道。 我相信每个认真的小说书写者对于小说这门技艺都各自有其深切的认识,他们之间最终不可调和的区别仅仅在于,写作是为了取悦他人抑或取悦自己,换言之,是依赖一些小聪明和花招,还是竭尽可能地忠实于自身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问题或许在于,小说家过分聪明而评论家过分不聪明。很多时候,那些聪明的小说家都太清楚评论家想要什么,虽然未必清楚自己最终想要什么。 于一爽清楚自己要什么。比如说一种松弛的语调和气息。当然有时候某种松弛也会成就另外一种造作,这种造作在年轻一代男性小说家的笔下屡见不鲜,他们习惯于把叙事者首先设置成一个男性废物,但却是有可能被女人莫名其妙垂青的废物,从而以一种反智主义的姿态来轻松赢得自己的魅力。所幸于一爽与此相去甚远。她的小说中的确充满了各种失败者的群像,但这种失败不是为了让叙事者获得某种类似无产者般的道德优势,相反,她是严肃的,对这些失败者痛彻心扉,但希望自己能够理解他们。 在于一爽这里,松弛首先意味着一种情感上的不作伪。那种被性欲奴役之后作自责呕吐状的政治正确,不属于于一爽,因为她相信,在庸常男女之间自愿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珍视和怜悯的,在这一点上,女作家似乎要比男作家勇敢,而于一爽更是其中较为勇敢的一员。她明白有些东西并非人性的弱点,而就是人性本身。她时常会超越性别的视角去静静地审视这一切,或是从他人的视角返观自我,她乐意呈现某种真实,言谈的真实、人类关系的真实乃至性事的真实,在生活之流中呈现。这需要天赋和反复的练习打磨。最终,松弛将走向准确,就像卖油翁将油准确地沥入狭窄的钱孔,而准确才是每一门技艺基本的道德。 迄今为止,于一爽写的都是短篇小说,其中都是同一种人,同一种状态,虽然他们分身为男人和女人。有时我在想,也许她把这些短篇中的素材融合成一部长篇小说,效果会更好一些,至少,她不用让她的主人公们一再地以某一方草草死去收场,在长篇小说中,他们只需要死去一次。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倘若要满足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她就势必要去编织或想象更复杂多变的情节,而由此势必招致的某种虚假,或许又是她很不愿意看到的。有时候,阅读她的小说的感觉有点像观看旋转木马,那些成年的男女以一种不太得体的方式坐在旋转木马上,不停地绕着一个很小的圆圈飞驰,这场景起初是有些荒谬的,但又是令人感伤的,她不知道拿这些荒谬和感伤该怎么办,也许她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很容易放弃的人,但这种放弃里面有一种极度真实的东西在。爱,对他们而言,既不是某种意义的开端也不是结尾,就像那些木马无所谓起点终点。他们如《玩具》中的叙事者王羞所言,"无法控制事情发展的不完整",但这种不完整中有一种极度真实的东西在。小说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忠诚于这种真实。 《死亡总是发生在一切之前》,是于一爽另外一个短篇的名字。死亡发生在一切之前而不是之后,这可以视作一种小说家的洞见。有一个古老的猜测,革命后的第二天会怎么样?与之类似,于一爽笔下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像在描写死亡后的第二天。那些衰弱和赤裸的魂灵还没有渡过卡戎掌管的冥河,还在河的这一边徘徊,他们不怀抱任何希望,却也没有剩下什么还值得绝望的。 接下来她要做的,或许就是要带他们渡过河流,给予他们新的烈火,以及新的生命。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假如她真的懂得"现代主义者永远不能与过去分手",那么她就应当试图去找回那些人的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她或许应当成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唯有如此,在河的对岸,地狱的某一层,那些人才会忽然自己开口,说话。 俄罗斯文学中有"多余人",我们的时代亦有这样一些异类,有时间、智力、机缘品尝社会巨变带来的成果(或后果)。不仅酒色财气,也文化艺术,更有甚者投身于死亡、挫败和虚无交织的游戏。和年轻一代的反叛忤逆不同,自我毁灭和孤芳自赏是这帮人的宿命,也是其自主的人生道路。一条道走到黑,个个都是这方面的专家老手。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揭示,赋予文学形式,于一爽大概是女作家中的第一人。特别是故意设计的见证人的角度,使于的讲述更具严肃性且真切可信。此外,她的写作还显示了一类好作家的诸多品性(有些是隐含的),比如克制、直接、专一,拒绝流行元素、主流话语,坚持抑制而非张扬知见才华。我相信,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层面,她的努力将会取得更加可观的回报。——韩东 她的小说再次证明了北京口语在操弄小说中所具备的先天优势。那种滑溜、机灵和生活现场感让人惊叹。她从最初就丢掉了经营文学的匠心和做作的"艺术考量"。她所着力的就是紧贴我们的肉身、匍匐于街头巷尾,裸露出当代生活乌糟、浑浊和伤感的真相。她的小说人物触手可及、体温犹存而又面目模糊。与其说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有什么意义,不如说她用他们表述了一种人类的存在形态。她是我见过的最为真诚同时又让我难以捉摸的女作家。——曹寇 在她的这些小说里,没有什么事是必须的,或者不得了的事,看起来有那么多的爱和性,只不过是大家来玩一下,过后不一定要忘记。每篇都有酒喝,酒好像是很重要的,她自己说:所有人物都会喝酒,但就是不知道酒是什么。所以我们才喝酒。写东西也如此。——小安 她小说里的男女都意识到"自己不重要","忘言"是她小说最最让人惊讶的特色,因为"忘言",她挣脱了"语言地心引力"的束缚,小说语言轻灵跳脱旁逸,叙述者似乎总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结果一跃成为说什么都好。这种语感,委实难能可贵。她本可以"姑妄言",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但她的警醒真诚又让她愈发克制。这种回流对应于小说人物内心静止的情感风暴,相得益彰,让人惊叹激赏。——赵志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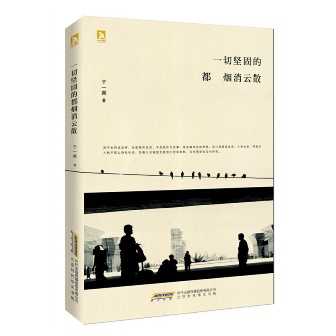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2:3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