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张新颖:沈从文的世界不拒绝任何人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ID:ibookreview 『与97000位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张新颖: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拒绝任何人 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来源:2014年7月19日《新京报》(此为访谈完整版) 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在大学里开设有“沈从文精读”、“中国新诗导读”等课程,沈从文研究正是张新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当代文学批评和随笔。张新颖1985年起就开始阅读沈从文,如今,其“十六年磨一剑”的着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得见天光,借此契机,这个在沈从文的世界中久久徘徊不愿离开的人,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深埋心底的沈从文,聊聊沈从文以外的人和事。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作者: 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真的历史是一条河”让我对沈从文的人生有了一个基本理解 新京报:很多人都说你已经是一个沈从文研究专家,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张新颖:我实事求是地认为,我不是专家。你要读懂一本书的话,可能需要读很多本书之后才行,反之,你想读懂很多本书,则要通过读懂一本一本的书才行。我不是一个(研究沈从文的)专家,这带给我的好处是,我不会把视线局限于这个单一领域。 新京报:这本大部头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在学术界颇受好评,据说这本书花费了您16年的心血? 张新颖:说我花了16年写成这本书,这种说法有点夸张,我并不是16年中都在干这一件事。1985年我开始读沈从文,但并未有写作想法。1992年,我读了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封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感觉必须写一写沈从文了。1997年,我写出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2002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32卷,一千多万字,其中四百万字生前没有发表过,这四百万字中的大部分又是1949年以来所写的——读完这些,我产生出强烈的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2005年我开始着手,但只写了一万多字,就因长期面对电脑而患了眼疾,便无法继续了。后来眼睛恢复了,但是被很多事情牵绊,写这本传记的事情便一拖再拖,成了我的心病。于是我在2012年秋天重新开始写,这期间的过程很顺利,因为材料已经在心里滚瓜烂熟,真正的写作过程只有一年。 新京报:《湘行书简》可以说是你研究沈从文的一个转折点吗?据说,你读到他1934年1月18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才感觉自己终于真正走进了沈从文的世界。你能谈一谈“真的历史是一条河”为何触发了你? 张新颖:《湘行书简》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它本来就是沈从文在一条河上写的东西,“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普通读者可能会把它当成自然景物描写,但其实这条河既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但人在这条河上生活,有船夫、有船娘……它和人的劳动、日常生活都连在一起,所以它又是一条“人”的河流。我从这里终于理解了沈从文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劳动、创作和智慧这些东西。这句话构成了我对沈从文人生的一个基本理解,以及他后半生为何钟情于杂文物的内心驱动力——那种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的折服。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拒绝任何人 新京报:大众可能只是会觉得沈从文后半生开始搞文物,由于政治或是命运里的无奈。你想通过这本传记告诉读者什么别的内容吗? 张新颖:大众对于沈从文的印象,可能会比较笼统,只知道他后半生开始搞文物研究,期间受过很多苦等等,对他的认识可能停留在对其命运的感慨上。而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沈从文后半生的“笼统”说清楚,所以我那么在意具体的事件和细节,为的就是清晰呈现他后半生的完整状态。此外,我觉得,对一个人的了解,单单停留在对他命运的感慨上,这很不够。有一些人会认为,沈从文很会明哲保身,建国以后他找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角落(杂文物研究)藏起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是这样的,我要写的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他仍然要去做出一番事业的决心。 新京报: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强盛的生命力? 张新颖: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能够贴近日常生活,贴近普通人的真情实感,他的文学不挑选读者。有的文学是挑选读者的,比如一些专业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书籍,只有学者才会阅读。但是沈从文的书,无论你是学化学还是学数学的,你不一定完全了解沈从文,或者只看过一篇文章,但是也会非常喜欢,这就是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拒绝任何人。当一种文学开始挑选读者的时候,它就把自己变小了。沈从文的文学不排斥普通的读者,这就是他的魅力。 再者,如果把历史时段拉长到五百年以后,再来写中国文学史,根本不会写到那么多作家。时间自动就把那些不够优质的部分过滤了。有的作家被过滤,有的作家在时间的过滤中反而凸显了出来。作家的价值,在时间过滤作用下,终会显露。 新京报:《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传记有个特点,“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沈从文自己的文字”,你“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但你自己也在“说明”中提到,“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但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这个“困难”指的什么? 张新颖:困难的地方在于,一个普通的读者阅读这本书时,需要不断地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之间转换,才看到立传者说的话,下一句突然出现引号里的内容,再下一句又蹦出一段既非沈从文又非写作者的第三人的引述,这样来回的跳跃造成不流畅的感觉,带来阅读的障碍感。如果我用写作者的第一人称叙述,把直接引语转化为间接引语,其实不难,但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任何的转化,哪怕再流畅也不能保证信息不扭曲、不流失。 ▲沈从文手绘图 对爱好的东西存敬畏心,不要轻易涉足 新京报:由于一直以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你在《迷恋记》的《小引》里把自己对外国文学的长期迷恋比作蜻蜓点水,自足于一种长期爱好者的状态,在《迷恋记》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段的引文,而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这些都可看出你对引文对于写作和阅读的作用十分看重,可以谈谈原因吗? 张新颖:(笑)我长得比较矮,习惯于从矮的角度看待事物。我们以往理解的研究者,往往站在一个“自以为”有高度的地方看待研究对象,用一种俯视或者说全景式的角度展开评论,或者是一种平等的角度和研究对象对话,这样的研究者很害怕在自己的身影在书中被淹没,显示不出自己的才华、观点。我不在乎这些,我本来就不具备这些,我不想在写作中把自己凸显出来,让人看见我的影子。更诚恳地说,即使在文本中,我没有直接“跳出来”,但在一个好读者那里,他会强烈地感觉到我的存在,而不用我自己去强调。 新京报:你身为文学评论家,为何对于“引”的重视超过对“评”的重视? 张新颖:我之所以对外国文学采取多“引”少“评”的方式,是因为我坚持要对每个专业之间的差异保持足够的尊重之心。一个人不能变成一个什么都懂,什么都谈的人。我那么热爱外国文学,所读之书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读专业书的数量,但它确实不是我的专业,看待它的方式就不够深入,所以,用“爱好者”这个词形容我对外国文学的感情,最为恰当。“爱好者”这个身份可能会有局限,但也会有好处——一个爱好者看待问题的特殊视角,有时会比专家更有启发性。我始终坚持,要对爱好的东西有敬畏之心,不要轻易去涉足。 新京报:你曾专文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这种深远影响甚至辐射到侯孝贤和贾樟柯等两岸电影导演,能否具体谈一下这种影响? 张新颖:侯孝贤在1983年拍《风柜来的人》这部电影前,已经有了很不错的两三部作品,但是他拍电影的态度是一种原始冲动式的方式——想说什么就拍什么。但在拍《风柜来的人》时,杨德昌等一群人从美国学习回来,告诉他,拍电影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侯孝贤就很苦恼,他虽不太理解这种“自觉”,但也意识到原始冲动式的方式(拍电影)已经走到困境,这个时候朱天文(《风柜来的人》编剧)给了他一本《从文自传》,他看完后恍然大悟,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字词句上的细节影响,沈从文给了侯孝贤一个观看世界、观看人生的全新角度,就像是摄影机的镜头。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在《风》以及后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侯孝贤阐释暴力、呈现普通人的生活都很有沈从文的痕迹。他特别强调,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残暴,多么不仁义,在太阳底下你总是会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真诚、朴素、温暖的情感。你不会斤斤计较于永远的暴力和黑暗,因为你关注了永恒存在的一种美,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拉开了。 后来的侯孝贤总是反复谈论沈从文,此时他正好处在创作的转折点上,需要确立其“自觉”拍电影的意识。沈从文的文学对侯孝贤的影响,是帮助其实现了“自觉”拍电影的方法、观念和世界观。杨德昌这批从美国学习回来的人所说的“自觉”,更多带有学院派电影理论启发的成分,而沈从文启发给侯孝贤的“自觉”,是教你从自己的经验来找看待世界的方法,坚持忠于自己的个人经验。 新京报:那贾樟柯呢?贾樟柯为什么看沈从文的书? 张新颖:贾樟柯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到《风柜来的人》这部电影,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何侯孝贤讲台湾小青年的故事和自己家乡小青年的故事如此相似?他为了弄明白,找来侯孝贤很多作品看,他发现侯孝贤总是在谈沈从文,贾樟柯是个聪明人,于是也决定好好阅读沈从文。于是,贾樟柯早期的作品如《站台》、《小武》等,其中对地方、对乡土人事的处理,带上了非常强烈的沈从文印记。贾樟柯最近的一部作品《天注定》,我观看以后特别强烈地想起沈从文。沈从文在40年代写《长河》,写现代“来了”之后的种种情形——家乡在时代压力下发生巨大的变化。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我要写这样一些人,他们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而《天注定》不就是想呈现人如何变成另一种极端的形式吗?这种对暴力、对极端性的处理,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处理得最多的。” 新京报:听说你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喜欢摇滚,而且架子鼓打得不错? 张新颖:架子鼓我的确会打,但其实是玩票的性质,喜欢摇滚也是年轻时候的故事了。我喜欢崔健,但是对摇滚的了解也就到张楚为止,之后就完全不了解了。摇滚的意义在中国和在西方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崔健出现时,他的意义不仅仅音乐,他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反抗的标志,但到后来(摇滚)概念逐渐缩小了,完全变成了流行音乐领域的事情,我对它的关注也就少了。 ◇记者手记 2014年7月14日之前,我与文学评论家张新颖素未谋面。作为一个文学评论的爱好者,我关注张老师有几年了,除了《迷恋记》、《此生》这两本读书随笔让我捧读玩味,那篇《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的长文我也曾拜读数遍,扎实细密的论述中渗透了对沈从文其文其人在动荡非常时期挣扎思索的无言敬意与慨叹。如今,张新颖“十六年磨一剑”的着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得见天光,我借着这个机会终于见了他本人。 酷暑难耐,下午我来到北京贝贝特公司所在的化工大院,七拐八绕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拐角的幽静院落。这里冷气开得很足,绿植种得很美,小院布置得素净雅致,两排木椅木桌非常认命地躲在院落一侧,我却因为炎热,都顾不得欣赏一下门厅里摆放的各式手工艺品,就钻进屋子里找沙发坐下。等了一小会儿,张新颖来了。我猛地一抬头,看见一个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正小喘气儿的中年人,他的右脸颊有一颗黑痣,嘴边挂着浅浅笑意,透过镜片可见眯起的眼睛里溢满了安详平和,见状如此,我略有紧张的心也松弛下来,我知道,从《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聊起,我还可以与张老师扯得更远一点。 ▲张新颖教授 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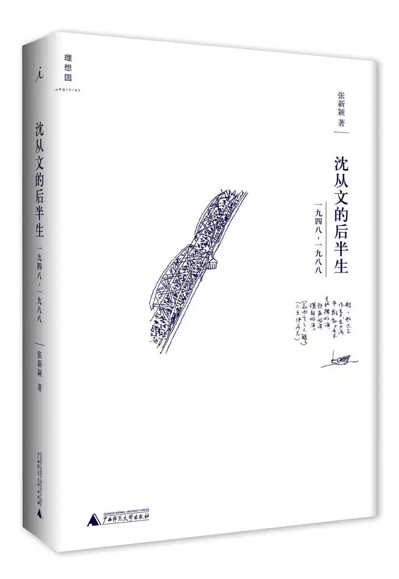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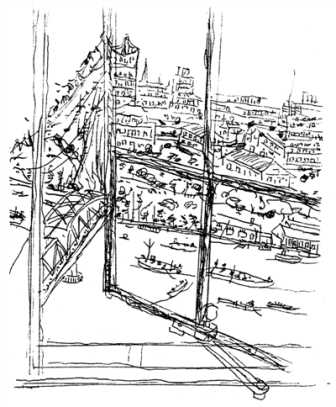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38:57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