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外刊扫描 文本、语境与光影:《傲慢与偏见》的身后故事
 |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 簡體 傳統 |
整理:刘亦凡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无论她事实上离我们有多远,“简姑妈”总是我们熟悉的。即便《傲慢与偏见》的世界早已远去不再,Darcy和Lizzy似乎仍是今日男男女女看待人间的一种方式。自1813年出版以来,《傲慢与偏见》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间的观感,究竟缘何发生,又怎样跌宕起伏、登堂入室,以至于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联系?下面的三篇文章,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蛛丝马迹。 第一篇文章选自Lambdin编着的奥斯丁研究指南。在这篇文章中,奥斯丁研究者Langland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角度入手,系统梳理了1813年至20世纪末,《傲慢与偏见》的“小世界”如何在象牙塔的光怪陆离中更迭变换。 第二篇文章则试图以历史解读的路径进入《傲慢与偏见》的文本,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国内关于民团扩张的政治论争出发,将《傲慢与偏见》理解为对这一争论无声的回应,从而为“疏离地理解”这部我们太过熟悉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陌生但又合理的视域。 第三篇文章聚焦《傲慢与偏见》影像改编的历程。通过对1940年以来七个影像版本的分析,作者既详尽揭示了我们最为熟悉的《傲慢与偏见》究竟所来何自,同时也提请我们思考,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阅读这部杰作,又当如何对待它被呈现出来的那些悲欢迷离。 小径分叉的花园 ——《傲慢与偏见》批评史200年 整理自:Pride and Prejudice: Jane Austen and Her Readers, A Companion to Austen Studies, pp.41-57 作者:Elizabeth Langland 伟大的切斯特顿曾说:世界是圆的,它是如此之圆,以至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个派别从一开始就争论,世界的位置是否上下颠倒了。 自1813年《傲慢与偏见》首版问世以来,奥斯丁及其写作艺术经历了与切斯特顿的世界如出一辙的遭遇。只不过,她的世界相较悲观与乐观者争讼不止的宇宙,无疑要小得太多。在狭小到几近无法转身的世界里,《傲慢与偏见》的早期读者早就奠定了针对奥斯丁的双元论调。夏洛特⋅勃朗蒂厌恶奥斯丁文明开化的花园,讥讽她不过是庸常事物的模仿者,一个未闻新鲜空气的小女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却将她的“小世界”视作对上帝造物的描摹。Lewes和Leigh称颂她在家室之间捕捉真理的卓越判断和基督徒的德性,Oliphant则在这部小说中发掘出专属女性作家的独立与质疑。 《傲慢与偏见》的世界太小了,它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它的早期读者总是要将视距拉远,而几乎注意不到这个世界里男男女女们的悲欢离合。直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普通读者》中前所未有地盛赞奥斯丁复杂的写作技巧,针对《傲慢与偏见》的傲慢与偏见才开始在20世纪逐渐进入更加细致的论域。不同于受益奥斯丁颇丰的亨利⋅詹姆斯,伍尔夫认为,奥斯丁的小说艺术绝不仅是对生活本真而无意识的描绘,相反,她倾注于人物的情感,她隐藏在文本表层之下的道德关切,才恰恰是一位作者对她生活其中的“小世界”用意入微的旨归。 伍尔夫颇具同情的评论洗刷了“头脑简单”的奥斯丁。然而,紧随其后的评论者对文本基石的发掘,仍然没能轻易跳脱先辈未死的视野。从Lascelles对《傲慢与偏见》在英国文学传统中地位的严肃论断开始(1939),直至70年代的《傲慢与偏见》研究都更像是不再愤怒的“简迷”们(Janeites)在语词和历史之间的游戏。以Ghent、Watt和Babb为代表的新批评家一方面拾弄起小说中富含道德意味的语汇,在诸如“随和”(agreeable)和“可亲”(amiable)的对勘中发掘奥斯丁对Jane和Lizzy道德性情的分辨褒贬,另一方面则以“庄园”与“财产”为支柱,检视小说开头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社会和历史中的表征与结构。在他们的努力下,奥斯丁的“小世界”不可思议地茁壮成长;旧世纪的支离感言拼成的夜语花园,也随之有被理论系统收编的倾向。只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辩坛此时已然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席卷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文化战场。 1979年,《阁楼上的疯女人》问世。吉尔伯特与古芭在这部“女性主义的文学圣经”里重新挑起了奥斯丁与勃朗蒂的嫌隙,使节制的前者和或可更节制的后者成为深陷挣扎纠缠的女性作家共同的母题。与先前的女性主义评论者(Spacks、Brownstein、Auerbach等人)不同,《疯女人》对《傲慢与偏见》的讨论没有从“女英雄”Lizzy或是Bennet一家的家庭秩序出发探索小说内在的性别主题,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关切点,在于奥斯丁和勃朗蒂作为愤怒的女性作者和怨怼的叙述者双重身份之间的纠葛与张力。根据这一视角,汲汲于礼俗嫁娶的“小世界”不是嗅不到新鲜空气的作者“头发长、见识短”的自我理解,而是愤怒的作者在面对压抑的社会时无可奈何的艺术构造。就一贯端庄合“礼”的奥斯丁而言,与其说她不过是个“小写的”、“不够愤怒的”女性作家,毋宁说她更倾向于揭示由女性和男性共同组成的社会究竟仍有何种缺陷。 缺陷总是存在的,然而相较于奥斯丁念兹在兹的“幸福”,Lizzy和Darcy世界中的缺陷似乎总是更加显眼。倘若7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阐释从某种角度回应了勃朗蒂在150年前的指责,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福柯式“思想系统史”风格在八、九十年代的浮现,无疑加深了《傲慢与偏见》“悲观主义”的那一面。 动用女性主义与福柯《性史》的理论资源,Kirkham、Johnson、Fryman等人“回到语境”的呼声率先使《傲慢与偏见》进入了现代英国史的政治、阶级和文化议题。延续前人面向世界的愤怒和象牙塔式的兴趣关切,这些同时深受文化研究影响的读者将《傲慢与偏见》和中产阶级、小说文体与女性意识在现代英国的兴起,18~19世纪早期英国经济结构乃至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从而彻底让维多利亚时代温良恭俭的读者黯然失色。在他们眼中,奥斯丁的“小世界”之所以“伟大”,压根不是因为是作者将节制的憎恶和敏锐的判断容斥在那格格不入的“大世界”之中,文本里的世界作为权力关系和阶级结构的产物,才是值得后人倾心仰慕、冷酷解剖的对象。用Fryman的话说,在《傲慢与偏见》和其他忝列“伟大传统”名单的小说纷纷搬上大众荧屏的时刻,这种关联对象和我们的方式,似乎也已成为我们之后的每个时代“唯一的方式”。 然而,无论我们是不是有些疯狂、但总体压抑而理智的“简迷”,一个必要的追问是:与奥斯丁“母女连心”的《傲慢与偏见》批评史,是否真的只剩下这一种书写的可能?从这本小说于1813年问世起,精英和大众、男人和女人、不相信乌托邦的和仍然相信乌托邦的,都在不断阅读它、讨论它、乃至憎恶它,以至于无论它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农庄,还是在21世纪的荧屏,都能容纳象牙塔浓妆淡抹的改编。 也许,奥斯丁一直是浑圆的,但这位看到“世界都脱了节”的“散文中的莎士比亚”并不曾告诉我们,“如何把它正过来”才好。在这个意义上,《傲慢与偏见》的“小世界”从来不是什么自在无碍的地球,它有待我们亲身涉足,需要依靠生活来检验。 陌生的读法 ——18世纪末军队论争和《傲慢与偏见》的历史语境 整理自:Sighing for a Soldier: Jane Austen and Military Pride and Prejudic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Vol.57, No.2 作者:Tim Fulford 倘若伟大作品之不朽源自“疏离感”的说法确凿无误,那么《傲慢与偏见》显然不能与荷马、莎士比亚并驾齐驱,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太容易发现自己熟悉的身影。扁平可笑的Collins、世故精明的Charlotte,乃至放纵轻浮的Lydia,都不太像是只有19世纪早期的英国水土才能孕育出来的男女。但倘若有人告诉我们,这些看似俯身可拾的人物恰恰源自奥斯丁对她的时代的回应,一部并不令人陌生的伟大作品,或许也会多出几分疏离。 在《傲慢与偏见》的世界中,乡绅、牧师和贵族都是构成底色的重要依据。透过De Bourgh夫人的目中无人和Collins先生的高头讲章,奥斯丁已多少借助Lizzy的目光向我们传达了这个世界的基本纹理。然而,在《英国史》作者麦考莱眼中一贯势利粗鄙的乡绅牧师之外,奥斯丁作为英国民团在地方扩张的见证者,或许对穿着红制服的军人更为印象深刻。1757和1778年两次英法战争之后,由诸如德文郡公爵等贵族征召的地方民团就开始漫步英国各地。在拿破仑和大革命的威胁下,到18世纪末英法再度开战时,英国东南部已然聚集了超过30万穿着红制服的军队,日夜操演、驻营、参加舞会。30年前还不过承担楚楚衣冠、仪礼庆典的民团,如今已成为乡村社会衣衫不整的常客。对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位Wickham的奥斯丁来说,这些事实想必不会陌生,更何况她还有一位哥哥曾于1796年大有离家从军之意。 相较De Bourgh和Collins这些传统势力的成员,驻扎民团的军人在奥斯丁写作《傲慢与偏见》的时期可谓一个全新的群体。与奥斯丁笔下的Wickham相似,大多数民团的军官和士兵都是脱离了原先生活圈的年轻人,在光线的军团制服和军队头衔之下,他们从前积攒的习性都与往日旧识一起淡出了自己生活的眼线,随之而来的,则往往是军队在地方舞会上的肆无忌惮和英国民众对国王军队的传统犹疑。 事实上,从1808年时任陆军大臣的卡斯尔雷提出重组民团法案开始,怀疑的声音就在辉格党人和普通民众之间普遍存在,尤其是在英国军队表现不利、上层军官又丑闻频出的时候,这些声音一度演化为政治争论的中心。奥斯丁自己就曾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倘若哥哥亨利在10年前成功参军,如今必然“要么命丧黄泉,要么个性扭曲”。 从事态的进展来看,一向洞若观火的奥斯丁此言非虚。正是在国会两党激辩卡斯尔雷法案的1808年,英军总司令约克公爵的情妇受贿鬻爵一案东窗事发,而穿着红制服的行贿者奉献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一场床笫之欢。一时之间,民情激愤,托利与辉格两党均将矛头指向了卡斯尔雷和那位倒霉的公爵。当时还经常撰写评论的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用他们一贯的热烈和沉郁断言道:贵族浪荡,国库贪墨,军队浮夸,不列颠何以对付拿破仑? 作为据说只知道闲聊和社交的“小妇人”,写作《傲慢与偏见》的奥斯丁虽确有迂回其事的嫌疑,却没有“视而不见”的冷漠。透过Lizzy的眼睛,她独辟蹊径又一如既往地在“找对象”这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下审视军人的一言一行。最初,我们只是在第7章知道,那一身身光鲜的红制服很快就让Lizzy的两个妹妹忘记了Bingley先生的相貌和财富,而到了第12章,我们又从她的叙述中得知,那些来路不明的军官里,有不少刚刚和他们有钱的叔伯共进了晚餐。当Lizzy的父亲正告女儿,这些来到Meryton笙歌燕舞的军官多半只会伤透本地女孩的心,我们马上就得到了一幅民团士兵和他们的迷恋者的共同肖像:轻浮,不自制,或许还要加上与Charlotte小姐全然不同的“没头脑的”势利。 当然,在Lizzy没有发现Wickham秉性的真相以前,这幅肖像仍只不过是一个待发掘的背景。相爱需要自我知识,而一个由旁观者组成的世界,往往会在不经意间遮蔽我们指向内心的目光。当Wickham在第17章对Lizzy讲述他身不由己的从军经历时,已经窥见肖像的读者或许会产生怀疑,因为Wickham看似深情款款的自白,很可能就是民团风气的剩余。然而Lizzy没有怀疑这一切,因为眼前的军官看上去是如此真诚地相信,自己沉沦下僚不是一己之力所为,而是动荡的时局、变迁的社会和旧识给予的不幸。在这个意义上,Wickham和所有民团的士兵一样,都将从军与过往的割舍,当作了此刻的自我随波逐流的理据。而对Lizzy和当地社会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Wickham们的迷失和可能带来的“伤心”,而是这些年轻人无从查起的自我和不畏人言的性情。 与Lizzy一样,直到Wickham和Lydia私奔的消息不胫而走,Darcy才真正理解了这种危险,和克服这种危险的知识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他对Wickham的认识虽要比Lizzy深入得多,但作为乡间秩序的守护者,他并未及时运用这种“知识”制止灾难的发生。相反,他和Lizzy一样,都满足于以所见充斥所知,而不轻易穿透所见做出评判,只不过映入Lizzy眼帘的,最先是这个谈吐随和、身世惨痛、穿着红制服的男人,而Darcy看到的,却是对方的出身、教养和家庭关系。当Darcy终于动用他与德比郡和伦敦的联系寻找Wickham和Lydia的踪迹时,知识的回归又最终彰显为在民团来临时失位的贵族良绅对自己身份职责的认识,以及时有“偏见”的Lizzy对所恋之人的理解。 我们无法断定,《傲慢与偏见》终局的安排,是否最终暗含了奥斯丁对理想地方秩序的重新勾画。但可以肯定的是,与Darcy和Lizzy这对佳偶相比,Wickham和Lydia自始至终不可能从彼此身上学到什么东西。也因此,基于历史语境的解释,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我们和《傲慢与偏见》的距离,但它给予我们更重要的教益可能是:奥斯丁在恳切面对她的世界时,既不是托利分子,也没有做辉格党徒。相较浩瀚经史和豪杰言行,“找对象”固然不能成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但若要寻找一把同样精深的标尺,多半也不会比“疏离”自我与他人来得容易。因为对我们常人来说,像Wickham和Lydia那样“任性”的生活,实在是过于轻松,也过于合乎“常情”。 当“小世界”遇上世界 ——影像改编中的《傲慢与偏见》 整理自:Pride and Prejudice, Jane Austen on Film and Television, pp.45-80 作者:Sue Parrill 看过了太多瞠目结舌的“经典改编”,Wickham先生的从军辩白就自会显出它的道理。尤其对那些反复登上银屏的“经典”而言,时代的更迭和原作者的远去,就更容易为“改编”这件暧昧之事找到离开故乡的正当性。 从1940年《傲慢与偏见》首度被翻拍为电影以来,这部小说在20世纪一共经历了七次银屏改编。由于深陷战事不能自拔,1940年的首次改编殊为离奇地没有由BBC接手承担,而是由美国的米高梅公司抢得先机。或许是出于民族感情,也许是英国文学教育已不得不依赖大众媒体,米高梅和 1949年NBC之后的五次改编无一例外,均由BBC操刀布阵。然而,英国人之所以能耐着性子反复翻拍,或许还有一个不能说的重要原因:那就是,米高梅“趁火打劫”的初版改编,实在过于糟糕了。 在这部长达117分钟的美国电影里,美国人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想象被凸显到了极致。在 “神经喜剧”的萧条时代风潮尚未褪尽的时刻,导演将Lizzy大胆地理解为一位“中产阶级”的女性,以至于饰演Lizzy的Greer Garson不仅活脱脱演得像个轻佻大胆的市井丫头,在Netherfield舞会这场关键的戏码中,Lizzy甚至违背原着情节拒绝了Darcy的邀约,并与并不在场的Wickham翩翩起舞。与Lizzy有关的支线人物也不例外:在小说中随和到近乎天真木讷的Jane被描摹为一个专擅调情的痴女,在与Bingley的交往中迅速凭借Lydia式的活泼得到青睐,而Lydia则和变身Bennet一家图书管理员的Collins一起,以夸张的笑声和肢体语言承担这部过头喜剧的粗壮神经。唯一看上去符合小说气质的角色,似乎也只剩下莎剧明星Lawrence Olivier饰演的Darcy。但鉴于Olivier的戏服全部来自《乱世佳人》剧组的存货,英国人在此剧出台之后的出离愤怒,则一点也不难理解。 米高梅版的《傲慢与偏见》在美国斩获了将近185万美元的惊人票房,但这个天花乱坠的战绩只能加剧本土“简迷”们的敌意。尽管1949年NBC改编的黑白电视剧在还原原着的格调上费尽心机,甚至在剧中安排了穿越时空的奥斯丁充当故事的叙述人,然而,英国人并不买账。1952年和1958年,BBC相继推出了两部六集的《傲慢与偏见》电视剧,出场的演员中,不乏日后以福尔摩斯形象塑造者闻名于世的Peter Cushing和简爱的扮演者Daphne Slater。相比尘嚣其上的米高梅版,这两部低调的改编虽然反响平平,但整体上紧凑地步趋了原着的情节,在取景和服装的选择上,BBC也终于让《傲慢与偏见》摆脱了肥皂剧式的精神短缺,维多利亚早期的服饰与布景开始广泛出现在屏幕之中,而到1967年BBC再度改编《傲慢与偏见》之时,萨默斯特和英国西部的外景风光,更为其平添一丝英国气息。 然而,此时的英国人并没有全然弃绝《傲慢与偏见》美国版本的全部要素。由于六集三十分钟的篇幅对《傲慢与偏见》而言多少有些紧凑,在外形靓丽的Bannerman和Fiander共同主演的1967年版电视剧里,不少源自米高梅和NBC剧本的改编桥段得到了相对节制的保留。例如,米高梅版中Lizzy、Darcy和Wickham同台出现的Netherfield舞会被编剧Lethbridge沿用,但与米高梅版不同的是,Darcy合乎情理地驱逐了Wickham,Lizzy也没有不讲礼貌地拒绝Darcy共舞一曲的请求;而NBC版中Darcy被提前的表白和自辩也在这部电视剧里出现,在省去了复述Darcy自白信内容的同时,Bannerman娴熟的表演也遮掩了Lizzy之后的摇摆不定与这一情节改编的冲突。 随着艺术史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主持的《文明的轨迹》彩色纪录片在1969年广受风评,BBC的名着改编就此进入了五彩斑斓的新时代。以15年为大致间隔,《傲慢与偏见》在1967年的迷你版之后一举成为彩色影视剧的热门改编题材,BBC二套与一套分别在1980年和1995年推出了两个系列改编剧。与尚显古朴的三个英国版本相比,二者都遵照全新的电视剧程设和光影技术,在正片之前安排了具有代表性的片头和主题曲。前者以水彩风格引出绅士淑女的生活场景,并伴之以轻快诙谐的背景曲,后者则以织锦、蕾丝面料和一只悠然缝织的玉手开头,同样古典灵动的钢琴小调似乎在提醒观众:你即将走进一个女人的世界。 在工心的古典风格和高度贴合原作的剧本之外,两部剧作在人物的塑造上同样超过了既有的各个版本。两位Lizzy的扮演者均属于美丽但不那么“一眼倾心”的类型,本着95版编剧“顽皮一点,吉普赛一点儿”(tom-boyish, gipsyish)的气质描摹和自身出色的角色理解,Elizabeth Garvie和Jennifer Ehle仅凭括辣松脆的台词步伐和刚柔交加的姿态眼神,就演出了Lizzy的才情、顽固和风趣。 同样无从辩驳的,还有95版主演Colin Firth对Darcy精准的再现和体会。在一次访谈中,Firth将这位年轻英俊的乡绅形容为“沉默寡言、高深莫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同时,总是随时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性情”,他同时强调,“Darcy没有说出口的”,和Darcy的所言所行同等重要。依靠这些于无声处的把握,Firth相较80版的男主角David Rintoul,更精微地勾画了Darcy“傲慢”形象的实际内涵。从Darcy与Lizzy初遇的舞会,到二人在Rosings庄园的心心相印,Darcy对待陌生人的傲慢性情经由Firth的神情交代,转而产生了这种“高贵者的性情”逐渐自省成熟的意味。在编剧Davies特意安排的几处桥段映衬下,在Olivier和Rintoul处略显呆板守旧的Darcy,于不经意间平添了许多迷人之处:最为“活色生香”的,莫过于Colin Firth穿着湿透的爱尔兰亚麻衫走出自家池塘、迎面撞上来访的Lizzy一幕。有不少人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95版《傲慢与偏见》收获的1100万收视率和席卷英国的“Darcy热”(Darcymania),完完全全是这一幕的“毒劳”。 尽管这种评论在剧作者和演员们看来,多少有些“米高梅式”的愚蠢和滥俗,但对今天的《傲慢与偏见》来说,这或许正是它最为恰如其分的处境。如果说80和95版的荧屏改编是它面向这个光影年华最不滥俗的方式,那么米高梅式的大制作和“大世界”的召唤,或将更可能是这部小妇人率性写就的岛国正典无从规避的诱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固然可以为谨严的英伦法度大唱颂歌,但我们却无权对米高梅进行品味和智识上的指摘。因为,Darcy和Lizzy的傲慢与偏见,终究不是我们对自己的时代持存傲慢与偏见的理由。谁又能不喜欢荧屏呈现给我们的Darcy呢?重要的事情也许是,Wickham和Collins在每个时代都会有,而往往是在喜爱Darcy和Lizzy并痛斥米高梅电影的人身上,他们的身影,从未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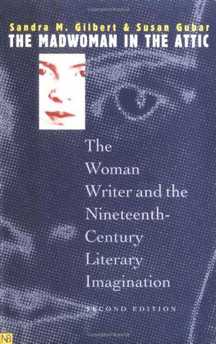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5:50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