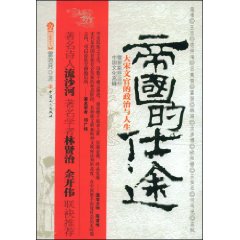|
相關閱讀 |
帝国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与人生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内容简介
《帝国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与人生》主要内容: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说是历史,是言必有据,不像当今众多对史事的戏说;说不全是历史,是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历史是一种延绵,但在《帝国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与人生》里,大可以古今通读。
编辑推荐
《帝国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与人生》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
媒体推荐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国学大师陈寅恪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着名学者邓广铭
如果想做官,劝你最好做宋朝的文官。好处多,一是“犯了错误”不打屁股,保有脸面;二是“上书言事”逆了龙鳞,不砍脑壳;三呢,嘿嘿,不瞒你说。俸钱还最可观。你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心特别善?非也。只因这兵痞皇帝的江山不是血盆里捞来,而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套取来的,就不免“外惧清议,内愧神明”,所以总想扮演三分慈眉善目,而标异于秦汉魏晋隋唐历朝的开国皇帝,更不用说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了。回想在下服劳役时,曾偷读不少宋人笔记,十分羡慕那时的文人处境。今又遥闻雷池月兄说宋朝的文官故事。益发添了鄙人的羡慕。
——着名诗人流沙河
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说是历史,是言必有据,不像当今众多对史事的戏说;说不全是历史,是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历史是一种延绵,但在这本书里,大可以古今通读。
——着名学者林贤治
雷池月先生是文化界知名学者,这些年来潜心于文化研究和历史随笔写作,卓有成就,颇有影响。他的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锐,文笔犀利。别具一格,融可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悦人耳目,非当下媚俗欺世之伪学者可比,弥足珍贵。
——着名学者余开伟
——国学大师陈寅恪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着名学者邓广铭
如果想做官,劝你最好做宋朝的文官。好处多,一是“犯了错误”不打屁股,保有脸面;二是“上书言事”逆了龙鳞,不砍脑壳;三呢,嘿嘿,不瞒你说。俸钱还最可观。你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心特别善?非也。只因这兵痞皇帝的江山不是血盆里捞来,而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套取来的,就不免“外惧清议,内愧神明”,所以总想扮演三分慈眉善目,而标异于秦汉魏晋隋唐历朝的开国皇帝,更不用说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了。回想在下服劳役时,曾偷读不少宋人笔记,十分羡慕那时的文人处境。今又遥闻雷池月兄说宋朝的文官故事。益发添了鄙人的羡慕。
——着名诗人流沙河
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说是历史,是言必有据,不像当今众多对史事的戏说;说不全是历史,是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历史是一种延绵,但在这本书里,大可以古今通读。
——着名学者林贤治
雷池月先生是文化界知名学者,这些年来潜心于文化研究和历史随笔写作,卓有成就,颇有影响。他的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锐,文笔犀利。别具一格,融可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悦人耳目,非当下媚俗欺世之伪学者可比,弥足珍贵。
——着名学者余开伟
作者简介
雷池月,原名雷逸湘,湖南嘉禾人,着有《宋太祖演义》《元世祖演义》《回首可怜歌舞地:古都史话》等。
目录
序言 文官的盛世:大宋帝国的开明政治
第一章 满汀洲人未归:寇准的三起三落
第二章 权力和道德的统一:贤相王旦的大事不糊涂
第三章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君子风范的楷模范仲淹
第四章 三天没生意,伙计吃伙计:吕夷简的政治宿命
第五章 帝国天空的双子星座:富弼与韩琦
第六章 失败的政治家:大宋文坛超一流才子苏轼
第七章 四朝元老,九旬宰相:古今独一无二的文彦博
第八章 楼高莫近危阑倚:面对道德尴尬困境的君子欧阳修
第九章 一个古典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千古一相王安石
第十章 惟有葵花向日倾:正直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
第十一章 对抗与合作:三位皇太后和文官的政治博弈
第一章 满汀洲人未归:寇准的三起三落
第二章 权力和道德的统一:贤相王旦的大事不糊涂
第三章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君子风范的楷模范仲淹
第四章 三天没生意,伙计吃伙计:吕夷简的政治宿命
第五章 帝国天空的双子星座:富弼与韩琦
第六章 失败的政治家:大宋文坛超一流才子苏轼
第七章 四朝元老,九旬宰相:古今独一无二的文彦博
第八章 楼高莫近危阑倚:面对道德尴尬困境的君子欧阳修
第九章 一个古典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千古一相王安石
第十章 惟有葵花向日倾:正直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
第十一章 对抗与合作:三位皇太后和文官的政治博弈
序言
公元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将拜占廷帝国打得落花流水,占领了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区域。教皇想借此机会恢复教廷统一的权威,竭力串联欧洲各国君主组织十字军东征收复圣地。那时西欧诸国的封建国家形态建立不久,国王没有权威,领主互相征伐,而跋扈且蛮横的领主和没有继承权的骑士们倒是希望乘此机会到东方去抢劫财物。因此,根本不能形成一支统一的队伍。好不容易第一次东征出发了,结果大军还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就作鸟兽散。总之,这时的欧洲,无论政治和经济都处于十分落后和混乱的状态。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实现了高度的进步、稳定和繁荣。民生的庶足且不说,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已被许多学者公认为封建社会的顶峰,尤其无与伦比的是在政治形态方面所独具的严谨而高效的文官制度。
北宋是公元960年开国的,到宋真宗即位的998年,这四十年的时间属于打基础的阶段。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优待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文官制度建设的政策一脉相承,到了真宗时期,成效已经彰显。此后的一百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高度繁荣的文化和规范的极具效力的文官政治,涌现了一大批才智卓异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大多出自“寒门”,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贡献突出——11世纪的百年间,历史的天空被他们点缀得何其绚烂!这百年间,中国出色的政治家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寇准、王旦、晏殊、吕夷简、富弼、韩琦、文彦博、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称得上名垂青史。
许多爱国情绪高涨的人,谈及我泱泱大国的悠久历史,总是有些不大愿意提起宋朝,仿佛那是一个让后人难以唤起自豪感的时代。确实,如果自豪感完全来自于诸如班超两入中亚、郑和七下西洋,甚至包括跟在拔都元帅后面横扫东欧这一类的宏大叙事,则赵宋一朝自然引不出什么合格的话题,因而只会遭遇到有意或无意的回避。
然而,这却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只要站在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民族历史逐段进行纵向的对比,就不难发现,单纯地从生存状态来衡量,北宋其实是最值得珍视和留恋的时代。这种比较因为涉及的方面太多,不可能十分具体细致,然而即使从前入粗线条的表述来分析,对这一百年的上述结论至少有以下诸点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撑。
国家的安定。这一百年没有让百姓流离失所的战乱。赵宋的统一战争都是在10世纪后期进行的,真宗即位以后和辽国的澶渊之战、仁宗时对西夏赵元昊和广西侬智高的战争,基本都在边境地区,而且规模不大,没有造成对全国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内部也再没有出现一百多年前那种可怕的军阀和流寇之间的混战。这种和平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本就十分稀有,更何况处在唐末五代和金人南下这两个悲惨的战乱时代之间,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安定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的开明。赵匡胤建国后,一直遵循保护和扶持知识分子的政治路线。在规范化的科举制度下,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高素质的文官队伍和它的代谢机制,从而构建了可延续的比较高效率的文官政府。由于言官的作用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政府的事权就较为明确,作风比较清廉。北宋的“党争”是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消极的影响不可避免,但是它并没有造成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后果,却带来了某些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必须检束自己的言行,以免为对立方提供进攻的口实。言官们表现活跃与否是衡量政治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赵匡胤交代了不许杀上书言事者,包括大臣和一般士人,后面的几任皇帝都没有突破这条戒律。能维持这一底线,宽松的政治环境就有希望了,不仅朝廷内部会形成敢言的政治风气,公共舆论也会得到充分的发育。
经济的繁荣。经过10世纪后四十年国家基础的夯实,结束了长期动乱的社会进入了周期性的快速发展通道。随着领主制经济在唐末的崩溃,中小地主阶级迅速成长,南方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垦殖和开发,手工业和商业也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跨入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一个依托于贸易物流、金融信贷、商旅饮食等服务产业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其生活质量相较北宋开封人也有一定差距。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见一斑:长安人没有夜生活,每个坊区都设有栅门,入夜就上锁,而开封饮食消费场所的服务通宵达旦、昼夜衔接。
文化的发达。由于科举制度的规范化,刺激了寒门士子通过文化检测跻身上层的欲望和追求。教育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推动,知识分子数量成倍数地增长。基数大,其中产生杰出人物的概率也就大,各个文化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极富创造力的大师。这点在文学和绘画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陈寅恪先生说北宋达到中国文化的巅峰时期确系不刊之论。
上述各点和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有密切关系,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首推政治的开明。北宋的几位皇帝——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概而言之,都很平庸。因为平庸,所以也不残暴。此外,还有三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政治上都堪称明智。帝国专制体制下,除了前秦的苻生、后赵的石虎那一类变态魔王,还有许多所谓明君英主,但其中也少有不残暴者,暴虐的程度虽有区别,但无不依赖杀戮手段来控制臣下,维持统治。因而,他们很难充分调动文官们的积极性,也很难让文官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高效率的文官运作体制也就无从谈起。这方面,北宋的几代帝、后的表现尽管平庸,但在仁政上,却称得上可圈可点。
大批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为文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11世纪涌现的杰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世纪。这些人才的综合努力,使北宋文官制度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亮点,对后世起到了重要的楷模作用。在文官制度的逐步健全中,君臣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当然这只是对比其他时代而言。皇权专制制度反人性的本质所带来的缺陷,终究不是文官们所能完全克服的。但从有效的文官制度和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百姓。
怎样来选定北宋文官的代表性人物呢?这个问题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我通过十一篇文字介绍了十四位主要人物,恰当与否?静候公议。原来还打算写狄青和包拯二位,最终放弃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真实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如在古典小说和民间传奇中那么大,写出来或许会贬损他们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包拯,一千年来,百姓对他的名字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和情感,怎么能让还原的真实去干扰人们追求公正的好梦。这群人里,有几位大文学家,我没有太多涉及他们的文学活动,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们是作为文官制度的代表人物被审视的,反映出来的当然主要是他们的政治表现。
这十几位人物,知名度都很高。各种媒体上都不难找到对他们或简或繁的介绍。因此,如果只是为了提供一些常见的史料和犹如教科书一类的评价,则此书的写作就显得没有必要了。我从事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也有些时日了,一直努力坚持一条,即对人和事,没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不能给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启发,就不要动笔。
我努力做到在这本书里不出现所谓“硬伤”,但就此作出绝对的保证是很不容易的。如有认真的读者能给我指出一二,我将非常感激。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实现了高度的进步、稳定和繁荣。民生的庶足且不说,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已被许多学者公认为封建社会的顶峰,尤其无与伦比的是在政治形态方面所独具的严谨而高效的文官制度。
北宋是公元960年开国的,到宋真宗即位的998年,这四十年的时间属于打基础的阶段。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优待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文官制度建设的政策一脉相承,到了真宗时期,成效已经彰显。此后的一百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高度繁荣的文化和规范的极具效力的文官政治,涌现了一大批才智卓异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大多出自“寒门”,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贡献突出——11世纪的百年间,历史的天空被他们点缀得何其绚烂!这百年间,中国出色的政治家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寇准、王旦、晏殊、吕夷简、富弼、韩琦、文彦博、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称得上名垂青史。
许多爱国情绪高涨的人,谈及我泱泱大国的悠久历史,总是有些不大愿意提起宋朝,仿佛那是一个让后人难以唤起自豪感的时代。确实,如果自豪感完全来自于诸如班超两入中亚、郑和七下西洋,甚至包括跟在拔都元帅后面横扫东欧这一类的宏大叙事,则赵宋一朝自然引不出什么合格的话题,因而只会遭遇到有意或无意的回避。
然而,这却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只要站在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民族历史逐段进行纵向的对比,就不难发现,单纯地从生存状态来衡量,北宋其实是最值得珍视和留恋的时代。这种比较因为涉及的方面太多,不可能十分具体细致,然而即使从前入粗线条的表述来分析,对这一百年的上述结论至少有以下诸点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撑。
国家的安定。这一百年没有让百姓流离失所的战乱。赵宋的统一战争都是在10世纪后期进行的,真宗即位以后和辽国的澶渊之战、仁宗时对西夏赵元昊和广西侬智高的战争,基本都在边境地区,而且规模不大,没有造成对全国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内部也再没有出现一百多年前那种可怕的军阀和流寇之间的混战。这种和平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本就十分稀有,更何况处在唐末五代和金人南下这两个悲惨的战乱时代之间,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安定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的开明。赵匡胤建国后,一直遵循保护和扶持知识分子的政治路线。在规范化的科举制度下,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高素质的文官队伍和它的代谢机制,从而构建了可延续的比较高效率的文官政府。由于言官的作用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政府的事权就较为明确,作风比较清廉。北宋的“党争”是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消极的影响不可避免,但是它并没有造成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后果,却带来了某些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必须检束自己的言行,以免为对立方提供进攻的口实。言官们表现活跃与否是衡量政治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赵匡胤交代了不许杀上书言事者,包括大臣和一般士人,后面的几任皇帝都没有突破这条戒律。能维持这一底线,宽松的政治环境就有希望了,不仅朝廷内部会形成敢言的政治风气,公共舆论也会得到充分的发育。
经济的繁荣。经过10世纪后四十年国家基础的夯实,结束了长期动乱的社会进入了周期性的快速发展通道。随着领主制经济在唐末的崩溃,中小地主阶级迅速成长,南方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垦殖和开发,手工业和商业也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跨入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一个依托于贸易物流、金融信贷、商旅饮食等服务产业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其生活质量相较北宋开封人也有一定差距。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见一斑:长安人没有夜生活,每个坊区都设有栅门,入夜就上锁,而开封饮食消费场所的服务通宵达旦、昼夜衔接。
文化的发达。由于科举制度的规范化,刺激了寒门士子通过文化检测跻身上层的欲望和追求。教育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推动,知识分子数量成倍数地增长。基数大,其中产生杰出人物的概率也就大,各个文化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极富创造力的大师。这点在文学和绘画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陈寅恪先生说北宋达到中国文化的巅峰时期确系不刊之论。
上述各点和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有密切关系,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首推政治的开明。北宋的几位皇帝——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概而言之,都很平庸。因为平庸,所以也不残暴。此外,还有三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政治上都堪称明智。帝国专制体制下,除了前秦的苻生、后赵的石虎那一类变态魔王,还有许多所谓明君英主,但其中也少有不残暴者,暴虐的程度虽有区别,但无不依赖杀戮手段来控制臣下,维持统治。因而,他们很难充分调动文官们的积极性,也很难让文官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高效率的文官运作体制也就无从谈起。这方面,北宋的几代帝、后的表现尽管平庸,但在仁政上,却称得上可圈可点。
大批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为文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11世纪涌现的杰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世纪。这些人才的综合努力,使北宋文官制度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亮点,对后世起到了重要的楷模作用。在文官制度的逐步健全中,君臣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当然这只是对比其他时代而言。皇权专制制度反人性的本质所带来的缺陷,终究不是文官们所能完全克服的。但从有效的文官制度和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百姓。
怎样来选定北宋文官的代表性人物呢?这个问题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我通过十一篇文字介绍了十四位主要人物,恰当与否?静候公议。原来还打算写狄青和包拯二位,最终放弃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真实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如在古典小说和民间传奇中那么大,写出来或许会贬损他们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包拯,一千年来,百姓对他的名字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和情感,怎么能让还原的真实去干扰人们追求公正的好梦。这群人里,有几位大文学家,我没有太多涉及他们的文学活动,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们是作为文官制度的代表人物被审视的,反映出来的当然主要是他们的政治表现。
这十几位人物,知名度都很高。各种媒体上都不难找到对他们或简或繁的介绍。因此,如果只是为了提供一些常见的史料和犹如教科书一类的评价,则此书的写作就显得没有必要了。我从事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也有些时日了,一直努力坚持一条,即对人和事,没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不能给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启发,就不要动笔。
我努力做到在这本书里不出现所谓“硬伤”,但就此作出绝对的保证是很不容易的。如有认真的读者能给我指出一二,我将非常感激。
文摘
苏轼在黄州待了五个年头,基本脱离政治,天天流连于山水之间,过从的也多是山夫野老,这倒为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机遇。这是他一生着述活动的巅峰时期,留下了大量为后人传颂的诗词歌赋。他在一个地名东坡的小山上盖了住房,并且开始使用东坡居士的名号,从此苏东坡三个字辉耀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光芒四射,千年不减。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被调往汝州,还是团练副使。全家二十余口,还没到目的地,盘缠就已经不济了。因为曾在常州置办了一点田产,苏轼打了个报告,要求准许他全家在常州暂住一段时间。神宗本不想把苏轼整得太狼狈,曾经数次想起用他,但总是被当道的大臣所阻格。这次调苏轼去汝州也是为了过渡一下,便于今后再行异动。神宗在手札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他想让苏轼主持修史的工作,宰相王琏“面有难色”。这些年苏轼名气越来越大,朝中敌视他的人不惟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神宗知道其中原委,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暂居常州的请求。
去常州的路上,经过南京,苏轼专程去看望了王安石。早年两人虽然政见不合,但并未翻脸。后来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还上表营救过自己,现在王已经下野多年,去看望他也没有攀附之嫌了。由于彼此都是政治上失意之人,许多观点变得接近起来。《宋史》中特别记录了两人之间的一段谈话,很有点意思。
(苏轼)日:“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日:“二事皆惠卿启之(指用兵和兴狱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搞起来的),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日:“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日:“安石须说。”又日:“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日:“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日:“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官员考核升迁的制度,任职满三年可获一次机会),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苏轼知道王安石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便从这点入手挑动他介入政治的热情,可是王也很老练,把账算在吕惠卿身上,自己不在其位不便说话。苏轼进一步从情感上激发他,说神宗对你可是千古少有的知遇之恩,你能推得掉吗?王的激情终于爆发,厉声表态自己要说话,但随后又要求苏轼不要把这话泄露给外人——他害怕卷入一个新的政治旋涡。接着苏轼把话题转向一般的道德说教,苏轼的回答像是玩笑,然而并不是玩笑:今天搞政治的人,为了升官,杀人都会干。王安石内心应该是同意这个尖刻的结论,但他只能报之一笑。他的地位已非昔日,苏轼的偏激所带来的凶险他也承受不起。
苏轼一家人刚刚来到常州,就传来了神宗的死讯。哲宗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很快,朝廷恢复了苏轼朝议郎的官位,授职登州太守。不久又召苏轼回朝廷任礼部郎中。命运的改变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反对变法的保守党人,当年得罪了新党分子而遭到迫害,苦大仇深,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肯定会恩怨分明忘我工作。可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苏轼对于一些保守党人那种“亲不亲,线上分”的观点和做法很看不惯,觉得新法也并非一无可取,而且,他和此时新党的领袖人物章悖、蔡确都有相当好的个人关系。这使一干保守党人逐渐将他视为异类。
元祜元年(1086年),苏轼刚调回中央不久,就是在蔡确的举荐下提拔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当时苏轼还有顾虑,觉得处境的变化跨度太大、太突然,便向蔡确请辞。可蔡确说:“你在外面倒霉了这么多年,什么官你不能当?朝里才干气魄谁能比得了你?”不仅不同意他辞职,还让他侍讲于延和殿,给年幼的哲宗当老师。蔡确的宰相位子随着旧党的翻身很快就丢了,被放到安州做知州。他心怀怨怼写诗讥讽太皇太后被人揭发,结果将被贬谪到岭南。这时苏轼给太皇太后上了一道密折,其中大意是:“如果朝廷不追究蔡确,则有损皇帝的孝道;如果朝廷重惩蔡确,则有累于太皇太后的仁政。最好的办法是皇帝下诏查处,然后太皇太后下诏赦免,这样就仁孝两全了。”虽然这道折子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说明苏轼在关键时候是有意要帮蔡确一把的。
章悖、司马光都是苏轼的朋友,但因为分别是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彼此自然势同水火。章悖为人跋扈。司马光刚刚回到中央时每每受他的欺侮,很苦恼。苏轼劝章悖不要这样,他说:“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刘备),法正日:‘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章悖觉得他说得有理,不再拿司马光开涮了。而随后司马光当上了宰相,新法全废,新党人物也逐个从要害位子上被撤换下来,苏轼对这些也都有看法。他还特别和司马光提到过废止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的问题,分析利害,希望司马光修订政策。司马光不以为然。不过由于几个月后司马光就死了,两人之间的分歧没有发展成为正面的对抗。
对于苏轼的这种旗帜不鲜明的政治态度,各方面都抱有不解或者不满。首先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太皇太后高氏,她不理解苏轼在新党掌权时代吃了那么多苦何以竟能不计前嫌,和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划不清界限,又不积极支持旧党的工作,难道他认为自己当年的遭遇完全是出于神宗的意愿?于是她带着皇帝召苏轼单独谈了一次话,《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提到了此事,文字简练而且生动:
太皇太后急问曰:“卿前年是何官?”(轼)日:“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日:“臣今待罪翰林学士。”“何以遽至此?”轼日:“遭遇太皇太后、皇帝(哲宗)陛下。”(后)日:“非也。”轼日:“岂大臣论荐乎?”日:“亦非也。”轼日:“臣虽无状,不敢自它涂以进。”太皇太后日:“此乃先帝(神宗)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日:‘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泣,帝(哲宗)亦泣。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被调往汝州,还是团练副使。全家二十余口,还没到目的地,盘缠就已经不济了。因为曾在常州置办了一点田产,苏轼打了个报告,要求准许他全家在常州暂住一段时间。神宗本不想把苏轼整得太狼狈,曾经数次想起用他,但总是被当道的大臣所阻格。这次调苏轼去汝州也是为了过渡一下,便于今后再行异动。神宗在手札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他想让苏轼主持修史的工作,宰相王琏“面有难色”。这些年苏轼名气越来越大,朝中敌视他的人不惟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神宗知道其中原委,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暂居常州的请求。
去常州的路上,经过南京,苏轼专程去看望了王安石。早年两人虽然政见不合,但并未翻脸。后来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还上表营救过自己,现在王已经下野多年,去看望他也没有攀附之嫌了。由于彼此都是政治上失意之人,许多观点变得接近起来。《宋史》中特别记录了两人之间的一段谈话,很有点意思。
(苏轼)日:“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日:“二事皆惠卿启之(指用兵和兴狱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搞起来的),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日:“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日:“安石须说。”又日:“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日:“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日:“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官员考核升迁的制度,任职满三年可获一次机会),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苏轼知道王安石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便从这点入手挑动他介入政治的热情,可是王也很老练,把账算在吕惠卿身上,自己不在其位不便说话。苏轼进一步从情感上激发他,说神宗对你可是千古少有的知遇之恩,你能推得掉吗?王的激情终于爆发,厉声表态自己要说话,但随后又要求苏轼不要把这话泄露给外人——他害怕卷入一个新的政治旋涡。接着苏轼把话题转向一般的道德说教,苏轼的回答像是玩笑,然而并不是玩笑:今天搞政治的人,为了升官,杀人都会干。王安石内心应该是同意这个尖刻的结论,但他只能报之一笑。他的地位已非昔日,苏轼的偏激所带来的凶险他也承受不起。
苏轼一家人刚刚来到常州,就传来了神宗的死讯。哲宗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很快,朝廷恢复了苏轼朝议郎的官位,授职登州太守。不久又召苏轼回朝廷任礼部郎中。命运的改变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反对变法的保守党人,当年得罪了新党分子而遭到迫害,苦大仇深,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肯定会恩怨分明忘我工作。可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苏轼对于一些保守党人那种“亲不亲,线上分”的观点和做法很看不惯,觉得新法也并非一无可取,而且,他和此时新党的领袖人物章悖、蔡确都有相当好的个人关系。这使一干保守党人逐渐将他视为异类。
元祜元年(1086年),苏轼刚调回中央不久,就是在蔡确的举荐下提拔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当时苏轼还有顾虑,觉得处境的变化跨度太大、太突然,便向蔡确请辞。可蔡确说:“你在外面倒霉了这么多年,什么官你不能当?朝里才干气魄谁能比得了你?”不仅不同意他辞职,还让他侍讲于延和殿,给年幼的哲宗当老师。蔡确的宰相位子随着旧党的翻身很快就丢了,被放到安州做知州。他心怀怨怼写诗讥讽太皇太后被人揭发,结果将被贬谪到岭南。这时苏轼给太皇太后上了一道密折,其中大意是:“如果朝廷不追究蔡确,则有损皇帝的孝道;如果朝廷重惩蔡确,则有累于太皇太后的仁政。最好的办法是皇帝下诏查处,然后太皇太后下诏赦免,这样就仁孝两全了。”虽然这道折子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说明苏轼在关键时候是有意要帮蔡确一把的。
章悖、司马光都是苏轼的朋友,但因为分别是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彼此自然势同水火。章悖为人跋扈。司马光刚刚回到中央时每每受他的欺侮,很苦恼。苏轼劝章悖不要这样,他说:“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刘备),法正日:‘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章悖觉得他说得有理,不再拿司马光开涮了。而随后司马光当上了宰相,新法全废,新党人物也逐个从要害位子上被撤换下来,苏轼对这些也都有看法。他还特别和司马光提到过废止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的问题,分析利害,希望司马光修订政策。司马光不以为然。不过由于几个月后司马光就死了,两人之间的分歧没有发展成为正面的对抗。
对于苏轼的这种旗帜不鲜明的政治态度,各方面都抱有不解或者不满。首先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太皇太后高氏,她不理解苏轼在新党掌权时代吃了那么多苦何以竟能不计前嫌,和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划不清界限,又不积极支持旧党的工作,难道他认为自己当年的遭遇完全是出于神宗的意愿?于是她带着皇帝召苏轼单独谈了一次话,《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提到了此事,文字简练而且生动:
太皇太后急问曰:“卿前年是何官?”(轼)日:“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日:“臣今待罪翰林学士。”“何以遽至此?”轼日:“遭遇太皇太后、皇帝(哲宗)陛下。”(后)日:“非也。”轼日:“岂大臣论荐乎?”日:“亦非也。”轼日:“臣虽无状,不敢自它涂以进。”太皇太后日:“此乃先帝(神宗)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日:‘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泣,帝(哲宗)亦泣。
雷池月 2011-04-13 20:31:2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