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新在何处?
 |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 簡體 傳統 |
撰文:金雁、秦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关于经济转轨,由于在几乎任何苏东国家它都是“代价最大”、“痛苦最多”的领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对派(无论什么“主义”者)都集中指责的领域。由于在多数国家右派与社会党都曾轮流执政,也曾因此轮流失去了指责的资格,而“新社会主义”者则一直处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独联体国家中的左派集中抨击的是原始积累的野蛮性与寡头垄断性,而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转轨相对较为规范,所以“新社会主义”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积累,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这又引出了他们对“后市场”体制即未来的“新型社会主义”的设想。 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与苏联地区的俄共一样对目前的转轨方向是否定的。但对未来的考虑,两者却有很大区别。俄共主流派认为目前的叶利钦体制是寡头独裁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实行“人民民主”,重建社会主义是久远的事。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尽管也抨击“右派专制”,但总体上并不否定东欧已实现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他们对“新型社会主义”更为关切。另一方面,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尽管也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但毕竟与旧体制乃至“俄罗斯思想”有更多的联系。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则更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希望实现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制的、建立在全球化而非民族传统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主义”。 虽然东欧“新社会主义”者更迫切希望搞社会主义,但另一个巨大的反差却是,他们的力量比本国的社会党和俄罗斯的俄共要小得多。俄共志在问鼎政权,而他们中的多数党连议会的门槛尚未踏入。因此他们一方面急于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成就,遗憾的是至今成效甚微,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淡化党与未来社会主义之关系的思潮,尤其是那些学者身份的无党派“新社会主义”者更是如此,沙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沙夫对以往的左派党,包括共产党和新旧社会党都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迄今为止波兰存在的执政党之所以成为特权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的活动经费由国库拨款,这就使在党的机关工作就是一项吸引人的工作;二是党统管国家干部的任命,使国家干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毫不奇怪,这两大保证使党处于社会的特殊地位。制度变革后这两大保障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除了。这就使新型政党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原来入党可以得到物质保障,也可以晋升到国家的领导岗位。现在呢?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党还会有吸引力吗?” 而西方类型的社会党已变成了一种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政党组织。“它使人有理由怀疑它究竟还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自‘二战’以后,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整个左翼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一些老牌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它们的革命语句,占据战前左翼社会党的阵地,而后者又占领了自由党的阵地,并实际上把自由党完全挤出政治舞台。” 因此现在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左派党,它的存在方式依各国国情会有很大差别,但沙夫认为有三点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个新型政党不再是按照列宁倡导的专政原则办事的党,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肯定是受人民拥护的(基于全民共识)制度,这种制度将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第二,在组织原则方面,它将遵循广泛的党内民主原则,给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党目的,那将不再是为了获得私利,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换句话说,那种靠党员的特权吸引人们入党的动机将完全消失,入党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 最近沙夫又强调,新左派不应当是一个政党,而应当是一种多元化的运动。“把新左派设想成政党的想法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恰恰有害”。这与他不久前主张“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新型政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沙夫现在认为左派运动中无疑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组织,但更应当包容当代新兴的各种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革命宗教运动。尤其是后者,目前受到苏东地区“传统左派”的普遍重视,从俄共到南共盟,从“极左”诸党到非党学者,都主张与之结盟。 如果说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其经验参考主要来自改革前的苏联史和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当代社会批判思潮的影响只占次要地位,那么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多数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其经验参考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萌芽”。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跨国公司的经济计划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南新共盟主席克尔斯马诺维奇就是个典型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论者,他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或者未实现,而应该说它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失败了。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下,使自己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价值。不管某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下。这个1/3的世界包括中国等未发生剧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社会。” 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与旧体制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有关,但他们也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观点,迅猛的新技术革命潮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变革,从而给“新社会主义”带来曙光,并且由于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这个过程并不遥远。克尔斯马诺维奇称:“当年世界的科学技术成果是人类难以估计的推动力。据统计有90%的发明创造是近30年来出现的,可以预计今后10~20年内,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将会增加一倍,在旧的关系条件下拥有这种能量,如果没有对于未来发展的设想,这本身就酝酿着可怕的文明风险。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地拥有这种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风险,而这种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担者,就是摆脱了历史的羁绊和冷酷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力量。” 而沙夫更宣称:新技术革命出人意料的飞跃有可能把因“现实社会主义”垮台使社会主义损失的时间大幅弥补回来。30年代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兰普曾说,如果以(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破产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推迟三四代人。“然而,现在的事态发展比兰普预计的要快得多,特别是世界上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这个时间可能大大缩短……世界向新型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的名称是否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发展的步伐亦将加快。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会到来,而且不会绕开波兰。所以,我们从现在就要孜孜不倦地努力迎接新型社会主义。”沙夫估计,尽管波兰“今天暂时还处在‘第三世界’行列中”,但只需20~30年,新技术革命就会使她“势必走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共同走的道路,即通向新型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为此大声疾呼:“20~30年时间很快会过去,我们再也不能错失良机。” 但这样一种“新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多数人心里并没有底,尤其是目前仍在向资本主义转轨的状况如何与技术革命的飞跃和“新社会主义”关系的出现相联系,更是令人困惑。基于目前尚处于“没有运动的思想”状态的“新社会主义”者在如此弱小的基础上如何迎接“新型社会主义”的来临,更是事关实践的大问题。一些“传统左派”的领导人坦承:“目前还未找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即在利润还未成为基本推动力的社会里,如何既保证有效的生产,又保证没有剥削,没有屈从和没有不平等的公正的社会关系。” 沙夫在世纪之交发表《论新左派的必要性》一文,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新社会主义”者中最为系统的看法。 在思想史上,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早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了自动化的进展将导致“工人阶级消失”这样一种“劳动的终结”说。沙夫接受并发展了这个观点并认为这是电脑时代“旧社会主义”消亡、资本主义终结和“新社会主义”兴起的最重要的动力。他认为,新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由此将引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变革:随着蓝领工人阶级的消失,继之而起的白领阶层并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什么高技术时代的新型无产者。因为在新时代知识就是资产,白领知识阶层便是有产者、中产阶层。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概念将会消失。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提供的技术手段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将使“科学的计划”成为可能和必要,“自由市场”体制将不可存在。 虽然劳动、剩余价值、无产者的消失改变了“剥削”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了社会矛盾。“因为这里不存在剥削人的劳动,但是却可以产生许多剥削人的新形式。”尽管“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将随着这种劳动的消失而消失,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将尖锐化,充分就业已经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绝不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而是减少就业。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失业正在日益严重,欧盟经济理事会已经通过决议,要在欧盟成员国中实行最低收入制。已经抛弃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然而沙夫认为,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下用社会保障来对付结构性失业是行不通的。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无业者中间重新分配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并没有触动问题的根本原因。甚至更加激进得多的做法,如欧盟开始实行的不管工作与否保证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决办法。从失业者的短期利益来看,这种措施显然值得称赞,但它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一旦由此产生的负担变得庞大时,即使最富有的社会也无法承受。此外,如果长时间采用这种措施,对社会尤其是对年轻人恰好是有害的”,它将培养懒汉,“引起社会的道德败坏”。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一种“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而不是产生利润的就业),也就是一种新式劳动,它以另一种方式从社会那里获得资金来源。这就需要新的社会产品分配制度,以便为那些被自动化和电脑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也就产生了一个“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 这就要求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只有当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被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就业代替时,人们才能应付现代转变的要求。这是一场改造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为社会所必需和认可的就业文明的转变。作为第一步,社会必须至少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1)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这是与失业不同的概念)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2)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同时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是发达世界的问题。因为第三世界到2000年将拥有世界人口的85%,那里的结构性失业具有爆炸性,“不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还会面临一场全球灾难”。因此,“新型社会主义”一旦发生,便是全球性的。 新技术革命一方面导致了“小就是美”、“在家上班”和高技术个体生产的可能,一方面造成了宏观经济计划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将不存在,由此产生的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上这一社会的动力及所要求的左派组织也将与传统大不相同。 (本文摘自《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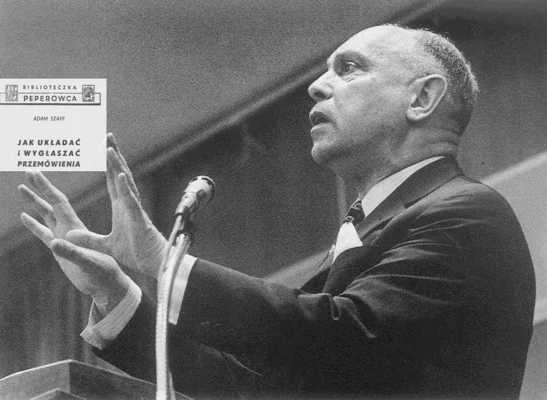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6:18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