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胡德夫●侯德健●罗大佑的音乐与人生
 |
>>> 深入傳統文化及個人修身養性 >>> | 簡體 傳統 |
6月18日,有“台湾首席文艺青年”之称的马世芳,在“看理想”(公众号ikanlixiang)的视频节目《听说》就将在优酷土豆和大家见面。马世芳是公认的台湾流行音乐最忠实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在总长16集的《听说》里,马世芳娓娓道来一首首歌、一个个音乐人的前身后世,在唤醒不止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时代的限制与变迁不胜唏嘘。马世芳的新作《耳朵借我》简体版也将同步上市,这是马世芳首部专讲“中文世界”的音乐文集,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听说》的来处。以下节选胡德夫、李双泽、侯德健、罗大佑的音乐与人生故事,让大家先睹为快。 胡德夫●侯德健●罗大佑的音乐与人生 文|马世芳 ●●● 美丽之岛 胡德夫、李双泽《美丽岛》 ▼ 二○一一年五月二日晚上,六十一岁的胡德夫——我们叫他Kimbo——在北京通州运河公园“草莓音乐节”登台献唱。舞台底下黑压压一大片人头,几乎都是二十啷当的青年。他们定定站着,双眼放光,一脸虔诚。这是“台湾舞台”的最后一段节目,同时会场两边大舞台的压轴表演也正火热:一边是“二手玫瑰”,另一边是谢天笑,暴躁的音浪自远方一左一右轰轰然辗过来。Kimbo没有乐队伴奏,他的武器只有一架键盘,和他的一把老嗓子。偶尔,年轻的口琴手小彭会蹿上台去吹几段,聊作帮衬。 当Kimbo粗壮的手指滑过琴键,开口唱歌,所有背景噪音瞬时像海潮一样退去。 我确实看过许多次Kimbo的演出。七○年代末我还是小学生,便曾在台北“国际学舍”或者“国父纪念馆”的演唱会上,看过一头黑发的青年Kimbo弹平台钢琴唱《牛背上的小孩》。我也曾在世纪初的台北“女巫店”看他唱歌,客人只有寥寥几桌。二○○五年他终于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在台北“红楼”剧场办发表会,那夜我也在座。三十年前的青春狂梦、二十年前的冲州撞府、十年前的憔悴落魄,尽成往事。台下冠盖云集,昔日战友多少恩怨情仇,如今许多已是台湾最有钱最有权的人。Kimbo开口唱歌,他们齐齐落泪。散场时那些翻脸多年、各事其主的头脸人物真诚地紧握双手,勾肩拍背,相约宵夜饮酒。仿佛起码这一个晚上,借着Kimbo的歌,他们可以回到世界还没那么复杂的时代。 经历过那些场面,我以为能经验的都经验过了,我将好整以暇听完这场演出。然而Kimbo唱起《美丽岛》。歌到中途,我发现自己正哗哗地流眼泪。我赧然抹了把脸,偷偷张望左右前后,他妈的,每个人都在抹眼泪,连音控台前的大哥也未幸免。 这大概是我不止第十遍听Kimbo唱这首歌,我以为《美丽岛》很难再让我哭了。打从八○年代末——台湾解除戒严、这首歌“开禁”的时代算起,大概有二十多年,我在任何演唱会听任何人唱这首歌都会掉眼泪。天知道,李双泽和梁景峰一九七七年写下《美丽岛》的时候,连一丝一毫悲壮的意思都没有呀。这原该是一首明亮、开阔、欢悦的歌。是后来发生的事,为它披上了苦涩的色彩。 Kimbo在台上说:“我最后来唱一首颂赞大地的歌,叫做《美丽岛》。”底下一片欢呼鼓掌,我暗暗吃惊于彼岸青年人对Kimbo与台湾乐史的熟悉,毕竟这首歌从未在此地公开发行。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唱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Kimbo豪气地说:“欢迎到台湾来!”全场欢声雷动。 我记得七○年代末的“校园民歌”演唱会,最后安可曲总是合唱《美丽岛》——那时这歌还没变成“党外杂志”的名字,大家不大把它跟政治联想在一起。七八岁的我听到“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总是忍不住咯咯笑。怎么会有人把香蕉和玉兰花写成歌词呢? 《美丽岛》的作曲人李双泽,是一个爱唱歌、爱写文章、爱画画、爱拍照、爱交女朋友的家伙。他大学没念完,赁居淡水一栋叫“动物园”的房子,淡江师生和各路艺文人士经常在那儿熬夜聚谈,俨然“沙龙”。他亦曾浪游世界,看遍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江湖风景。李双泽最着名的事迹,是在一九七六年一场校园演唱会拎着一瓶可口可乐上台,质问唱“洋歌”的青年:“全世界年轻人都在喝可口可乐、唱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传说他后来一气掷碎了那瓶可乐,但据当天在场者回忆,那恐怕是夸大的神话。无所谓,李双泽的“呛声”,震撼力并不下于当众打碎一只玻璃瓶。 既然点了火,他也以身作则,开始写歌,并用简陋器材录下一些作品。一九七七年九月,李双泽跳海救人,竟溺死在淡水,时年二十八岁,他甚至来不及自己录下亲自演唱的《美丽岛》。告别式前一天,老友Kimbo和杨祖珺借用“稻草人”西餐厅的录音器材,就着李双泽的手稿弹唱这首歌,留下了《美丽岛》的第一个录音版本,在葬礼现场初次播放。这个版本后来屡经转拷,地下流传许多年,直到二○○八年才正式收录到杨祖珺《关不住的歌声》专辑。 我偶尔会想:设若早生二十年,我会变成李双泽的哥们儿吗?大概不会。李双泽是一个倔强、热血、满心正义感的家伙,并且就跟许多那个岁数的青年一样,深深相信自己看到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若是身在一九七六“可乐事件”现场,我想,我不会为他的唐突与无礼喝彩。 我在青年时代也认识同样倔强、热血、满怀正义的同辈人,他们才气确实远不如李双泽,我总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幽默感,他们深深相信自己可以改造世界,凡不这么相信的人则必须被改造。他们刻意不修边幅,个个活成浪人模样,仿佛这样就可以摆脱他们多半不坏的出身,假装自己属于那个他们从未属于过的阶级。他们崇尚“草根”的土味儿,崇尚“素人”与“民间”这样的词汇,敌视精致、敌视文气、敌视“为艺术而艺术”。他们认为在这危急的时代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他们随时要“启蒙”你。而我始终觉得所谓自由,就是让人能有“置身事外”的权利。一旦我们变得和我们反抗的对象一样无趣、满嘴教条、随时随地逼人表态,那革命还有什么意思?——不消说,我们看彼此都不是很顺眼。 听着李双泽那些粗糙的老录音,我不禁想起青年时代认识的那些人。若我与李双泽生在同一时代,多半也会被他目为“觉悟性不够”、“革命纯度不足”的那种人吧?设若如此,我该感到羞愧吗? ●●● 巨龙之眼 侯德健《龙的传人》 ▼ 看胡德夫的前一天,我在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看了整场“滚石三十年”演唱会。其中一个饶富深意的段落,是侯德健和李建复同台唱《龙的传人》——李建复是这首歌的原唱,至于侯德健,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已经二十多年未曾在大陆公开演出了。那段表演不算特别纯熟,恪于时间压力,歌曲没能唱全,老侯还唱错了一段词。但当李建复介绍侯德健出场,唱了两句《归去来兮》,仍让我心震动: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 是多少年来的徘徊 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 是多少年来的等待 啊,究竟颤抖了多少年 侯德健,还认识这个名字的两岸青年恐怕不多了。然而只要回头专心听过,你应该也会同意,他实在是七○年代“民歌运动”孕育的那群青年创作人之中,才气、底气俱足的将才。他的创作很早就脱去了彼时“校园民歌”习见的文艺腔,语言干净而坦率,并且擅长从“小我”经验写出“大我”情结。比方后来让包美圣唱红的《那一盆火》: 大年夜的歌声在远远地唱,冷冷的北风紧紧地吹 我总是痴痴地看着那,轻轻的纸灰慢慢地飞 曾经是爷爷点着的火,曾经是爹爹交给了我 分不清究竟为什么,爱上这熊熊的一盆火 别问我唱的什么调,其实你心里全知道 敲敲胸中锈了的弦,轻轻地唱你的相思调 侯德健生于一九五六年,比李双泽小七岁。他曾说:“政治本该是人的一部分,人不应该是政治的一部分。”——然而事与愿违,侯德健半生浪荡颠簸,几乎都和“政治的一部分”难分难解。他老是在错误时机做正确的事、在错误场合说正确的话,结果这个名字就这样曲曲折折跌进了历史板块错开的裂缝,被海峡两岸以各自不同的理由遗忘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国宣布将在次年元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是台湾自一九七一年被赶出联合国以来,连年对外关系挫败的最后一击。二十二岁的侯德健在这一天写下《龙的传人》——说真的,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粗糙,绝非侯德健最讲究的作品。但是一首歌的命运,往往连创作者都无法逆料。侯德健做梦也想不到这首歌将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带给他多少光荣和诅咒。 《龙的传人》先以手抄曲谱的形式传唱开来,继而在一九八○年由李建复录成唱片。将近三十年后,我初次听到侯德健一九七九年亲自弹唱的demo,才发现《龙的传人》原本是一首哀怨而压抑的民谣,与我们熟悉的悲壮情绪相去甚远。当年是制作人李寿全和编曲家陈志远,合力把这首歌“托”了起来:悠扬的法国号前奏、沉郁跌宕的混声合唱、浩荡的管弦乐团……当然还有李建复正气凛然的清亮歌声。他们让《龙的传人》彻底摆脱哀怨,变成了一首悲壮的史诗。 QQ音乐没有侯德健版《龙的传人》,此处为纯音乐版。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 这是一个在台湾出生、成长的眷村子弟,对素未谋面的“故土中国”的执迷。我们想起杨弦唱过的余光中《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长江黄河对彼时的台湾青年,仍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符号。 此为罗大佑版,QQ音乐没有杨弦版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在“鸟巢”九万人的会场,再度听到这久违的熟悉的歌词,仍不禁感到错乱。历经三十年岁月冲刷,物换星移,如此单薄天真的图腾标签,在我耳中益发显得不合时宜。 而那天在“鸟巢”,他们没能唱到关键的第三段: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姑息的剑”是为了配合审查而改的词。侯德健更早的版本有二:“洋人的剑”或者“奴才的剑”。“洋人”指列强逼压,“奴才的剑”则把责任归到了不争气的“自己人”,更耐人寻味一些。 整首歌直到这边才转入悲愤。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耻辱,和台美“断交”、洋人“背弃”这片岛屿的现实前后映照。严格讲,这段歌词潦草而文气不通,但正是这暧昧的仇愤,让《龙的传人》能够跨越两岸、在不同的时代凝聚起不同的群众——它勾起了“同仇敌忾”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这在台美“断交”之后被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台湾,以及迈入改革开放、重返世界舞台的大陆,都能找到集体焦虑的连接点。于是它先被国民党“绑架”成官媒炒作的“爱国歌曲”,直到侯德健一九八三年干犯禁忌“出走”大陆,《龙的传人》在台湾一度变成禁歌。在此同时,它开始在对岸传唱,相同的词曲,却能映射出另一种光谱。 三十多年过去,台湾是老早告别《龙的传人》的意识形态了,而我深深觉得彼岸亦未必需要这条身姿暧昧、体腔空虚的巨龙。见到侯德健终于得以公开登台演出,我衷心为他欢喜。然而老实说,同样关于历史和家园,我更愿意再唱一次《美丽岛》,再听一次《少年中国》。我还更愿意拿出蒙尘的老唱片,再放一次侯德健“出走”对岸之后写的《歌词一九八三》,那年老侯二十七岁: 回想起当年,没问完的问题很不少 只是到如今,还需要答案的已经不多 关于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 关于一八四○以及一九九七 以及关于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于太右而太左 以及关于曾经瞻前而不顾后, 或者关于顾后却忘了前瞻 以及或者关于究竟哪一年,我们才能够瞻前又顾后 或者以及关于究竟哪一天,我们才能够不左也不右 ●●● 白色的恐惧,红色的污 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 甲午战争百余年来,台湾不断接受外来文化与新移民的刺激,遂也渐渐习惯了“混血”式的文化样态。台湾曾经戒严近四十年,然而针对文化内容的管制,较诸政治体制的压抑,相对还是宽松一些,舶来文化商品繁多。到七○年代“寻根”风起,青年世代重新摸索“身份认同”,首先要面对的,也是这盘根错节的“混血”情结。 一九七一年奚淞、黄永松、吴美云、姚孟嘉创办《汉声》杂志英文版,一九七七年改为中文版,深入探讨古迹保护、民间艺术与庶民文化。一九七三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高信疆接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提拔新锐作家,推行报道文学,引介素人画家洪通、恒春老歌手陈达。一九七五年歌手杨弦在中山堂开演唱会,出版专辑,替余光中的现代诗谱曲,点燃“民歌运动”。一九七六年李双泽在淡江大学演唱会手持可口可乐,怒道“走遍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洋文歌”,遂令“唱自己的歌”成为广为流传的精神口号。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深化、普及了“寻根意识”,同年“金韵奖”创办,“青年创作歌谣”风潮彻底改变了华语乐坛的走向。 这些事件,都有一股纯粹近乎天真的底气。事起之初,都未必想象得到后面将引出多么不得了的效应,更未必有“运动”的自觉。在台湾对外关系节节败退的时代,青年有强烈的危机感,也有巨大的使命感。他们未尝经验过父母辈叨念的战乱岁月,拥有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得以探索兴趣,甚至将兴趣发展成专业。当局高喊“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时代,青年人一方面深受舶来文化的“混血”影响,对西洋与东洋的青年文化深自向往,一方面又体会到台湾仰“上国”鼻息之可悲,而产生出民族主义的意气和“寻根”的焦虑。 要理解这样的纠结,我们可以用一首歌来说说: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的父亲是苗栗客家人,母亲是台南人,但他从小在台北长大。一九八三年,罗大佑发行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A面第二首歌便是《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当年歌词页,《亚细亚的孤儿》有一行副标“致中南半岛难民”——七○年代越战结束,许多人从海路出逃,舢舨、渔船搁浅在南中国海的珊瑚礁,饿死渴死者众,竟还有人相食的惨事。那样的故事,成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对内最好使的“反共教材”。 然而,只要你知道“亚细亚的孤儿”一词出处,便明白那“致难民”的副标是障眼法。《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作家吴浊流一九四五年完稿的长篇小说:一个叫胡太明的台湾青年,在家乡受日本殖民者欺压,日本留学归来却被乡人排挤,赴大陆又被视为外人,终被逼疯。罗大佑借用这个意象,开篇四行歌词,竟仿佛已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一路走到了国共内战与岛屿长年的戒严。 罗大佑是在当医师的父亲书架上看到了《亚细亚的孤儿》,那一刹那,他脑中响起了副歌吟哦的旋律。罗大佑的父亲曾在日治时代被派去南洋当军医,一千个台湾兵只有三百人活着回来。后来国民党败退迁台,政权危殆之际下重手镇压异己,开启了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父辈大半生承受不同政权的时代动荡,“胡太明”的命运非但是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也预告了后来苦涩的历史。 假使不加遮饰,光凭“白色的恐惧”一句,在戒严时代,罗大佑很可能从此无法出唱片——那“致难民”的副标,表面迎合了执政者的“主旋律”,暗地却为所有懂得“解码”的人,偷渡了一则历史的大叙述。 这首歌背后的曲折,反映七八十年代台湾创作人的处境:严密的审查制度之下,创作人必须苦心设计“偷渡”路线,埋藏“暗号”,气味相投的听众得设法从字里行间“嗅出”那密码。当一首这样的歌透过电波向四方播送,那“启蒙”的暗号,便可能改变不只一小撮人的生命: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这是早期罗大佑最好的歌词,语言直白而不失诗的质地,一洗“民歌”习见的学生腔、文艺腔,正如“民歌”一洗早年流行歌词的歌厅气、江湖腔。然而罗大佑在开创中文歌词新局的同时,亦曾陆续以余光中、郑愁予、吴晟诗作谱曲,其实承继了“民歌”时代“以诗入歌”的传统。那一辈“知识青年”背景的歌人常以“文艺青年”自居,他们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也为这新起的“歌坛”铺垫了起码的“文化教养”。 重听《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知道:创作人在全新的时代,骤临无穷的机会与风险,他们几乎没有前例可循,仍企图以“大众娱乐”为载体,“偷渡”理念,实现理想。禁忌松动,民智渐开,大家对任何新鲜的文化产品都充满好奇,近乎饥渴,我们还来不及体会后来“信息过剩”引致的饱胀、厌烦与虚无。“流行歌曲”作为“创作门类”的潜能获得社会共识,“唱片人”亦得以拥有“文化人”的自尊与气魄。对跃跃欲试的创作者,那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作品一旦多起来,台湾流行音乐遂能挟其跨界混搭之杂色,以庶民文化“火车头”的姿态向整个汉语文化圈辐射,终于成为这片岛屿有史以来影响最深最巨的“文化输出”。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禁忌不再,《亚细亚的孤儿》那行“致中南半岛难民”的副标,也在后来的版本拿下了。但故事并未结束——二○○三年,罗大佑全套作品首度在大陆发行正版,《亚细亚的孤儿》却从唱片和歌词内页消失,只剩一行标题。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

胡德夫顶着满头白发在草莓音乐节舞台上边弹边唱
演奏中的胡德夫
苏娅版《美丽岛》。腾讯没有收录胡德夫版,很可惜。
英年早逝的《美丽岛》作曲者李双泽
胡德夫(前排右一)、李双泽(后排右一)
李建复 - 归去来兮 (1980)
侯德健(右)和李建复。“滚石三十年”演唱会上。
包美圣
侯德健
1988年春晚 侯德健《龙的传人》。侯德健次年因政治原因无缘大陆舞台二十一年。该视频似乎无法加载到微信。读者可在网页版查看。
台湾新民歌之父杨弦
老磁带。侯德健作品集。
罗大佑
汉声四君子,左起:姚孟嘉、奚淞、黄永松、吴美云
《未来主人公》封面
一九八三年出版《未来的主人翁》内页,《亚细亚的孤儿》仍有“致中南半岛难民”副标题。
罗大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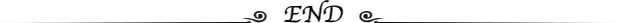
理想国 马世芳 2015-08-23 08:54:37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