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 一日一书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悲伤与理智 作者: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刘文飞译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5-4 首先,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布罗茨基断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战利品》)。他认为,不是艺术在模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模仿艺术,因为艺术自身便构成一种更真实、更理想、更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悲伤与理智》)“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他在他作为美国桂冠诗人而作的一次演讲中声称:“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学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的语言学和进化论灯塔。”(《一个不温和的建议》)阅读诗歌,也就是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感化作用,这能使人远离俗套走向创造,远离同一走向个性,远离恶走向善,因此,诗就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狗咬狗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词,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表情独特的脸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名命题,即“美将拯救世界”,也不止一次地重申了他自己的一个着名命题,即“美学为伦理学之母”。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做的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是其美学立场的集中表述,演说中的这段话又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关于艺术及其实质和功能的看法: 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一位研究者指出:“约瑟夫•布罗茨基创作中的重要组成即散文体文学批评。尽管布罗茨基本人视诗歌为人类的最高成就(也大大高于散文),可他的文学批评,就像他在归纳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所说的那样,却是他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之继续发展。”关于语言,首先是关于诗歌语言之本质、关于诗人与语言之关系的理解,的确构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他将诗歌视为语言的最高存在形式,由此而来,他便将诗人置于一个崇高的位置。他曾称曼德施塔姆为“文明的孩子”,并多次复述曼德施塔姆关于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的名言,因为语言就是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创造中唯一不朽的东西,图书馆比国家更强大,帝国不是依靠军队而是依靠语言来维系的,而诗歌作为语言之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组合形式,无疑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而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空间和遗忘,为人类文明的积淀和留存作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布罗茨基又继承诗歌史上传统的灵感说,夸大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是语言在使用人类,而不是相反。语言自非人类真理和从属性的王国流入人类世界,最终发出这种无生命物质的声音,而诗歌只是其不时发出的潺潺水声之记录。”(《关爱无生命者》)“实际上,缪斯即嫁了人的‘语言’”,“换句话说,缪斯就是语言的声音;一位诗人实际倾听的东西,那真的向他口授出下一行诗句的东西,就是语言。”(《第二自我》)布罗茨基的诺贝尔奖演说是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的: 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最后,从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对于具体的诗人和诗作的解读和评价中,也不难感觉出他对某一类型的诗人及其诗作的心仪和推崇。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讲坛上,布罗茨基心怀感激地提到了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五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马托娃和奥登。在文集《小于一》中,成为他专文论述对象的诗人依次是阿赫马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莱、曼德施塔姆、沃尔科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等七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他用心追忆、着力论述的诗人共有五位,即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这样一份诗人名单,大约就是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大诗人名单了,甚至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布罗茨基对弗罗斯特、哈代和里尔克展开长篇大论,关于这三位诗人某一首诗或某几首诗作的解读竟然长达数十页,洋洋数万言,这三篇文章加起来便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布罗茨基在文中不止一次提醒听众,他在对这些诗作进行“逐行”解读:“我们将逐行分析这些诗,目的不仅是激起你们对这位诗人的兴趣,同时也为了让你们看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个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堪比《物种起源》里描述的那个相似过程,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还要说它比后者还要出色,即便仅仅因为后者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而非哈代先生的诗作。”(《求爱于无生命者》)。他在课堂上讲解弗罗斯特的诗时,建议学生们“特别留意诗中的每一个字母和每一个停顿”(《悲伤与理智》)。他称赞里尔克德语诗的英译者利什曼,因为后者的译诗“赋予此诗一种令英语读者感到亲近的格律形式,使他们能更加自信地逐行欣赏原作者的成就”(《九十年之后》)。其实,布罗茨基不止于“逐行”分析,他在很多情况下都在“逐字地”、甚至“逐字母地”地解剖原作。他这样不厌其烦,精雕细琢,当然是为了教会人们懂诗,懂得诗歌的奥妙,当然是为了像达尔文试图探清人类的进化过程那样来探清一首诗或一位诗人的“进化过程”,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在告诉他的读者,他心目中的最佳诗人和最佳诗歌究竟是什么样的。布罗茨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学生后来在回忆他这位文学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布罗茨基并不迷恋对诗歌文本的结构分析,我们的大学当时因这种结构分析而着称,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娜常常从法国来我们这里讲课。布罗茨基的方法却相当传统:他希望让学生理解一首诗的所有原创性、隐喻结构的深度、历史和文学语境的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他试图揭示写作此诗的那门语言所蕴藏的创作潜力。”在关于弗罗斯特《家葬》一诗的分析中,布罗茨基给出了全文、乃至全书具有点题性质的一段话: 那么,他在他这首非常个性化的诗中想要探求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他所探求的就是悲伤与理智,这两者尽管互为毒药,但却是语言最有效的燃料,或者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它们是永不退色的诗歌墨水。弗罗斯特处处信赖它们,几乎能使你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将笔插进这个墨水瓶,就是希望降低瓶中的内容水平线;你们也能发现他这样做的实际好处。然而,笔插得越深,存在的黑色要素就会升得越高,人的大脑就像人的手指一样,也会被这种液体染黑。悲伤越多,理智也就越多。人们可能会支持《家葬》中的某一方,但叙述者的出现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当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代表理智与悲伤时,叙述者则代表着他们两者的结合。换句话说,当男女主人公的真正联盟瓦解时,故事就将悲伤嫁给了理智,因为叙述线索在这里取代了个性的发展,至少,对于读者来说是这样的。也许,对于作者来说一样。换句话说,这首诗是在扮演命运的角色。 在布罗茨基看来,理想的诗人就应该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理想的诗歌写作就应该是“理性和直觉之融合”,而理想的诗就是“思想的音乐”。 《悲伤与理智》中的每篇散文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关于诗和诗人的观照,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抱合,构成了一曲“关于诗歌的思考”这一主题的复杂变奏曲。在阅读《悲伤与理智》时我们往往会生出这样一个感觉,即布罗茨基一谈起诗歌来便口若悬河,游刃有余,妙语连珠,可每当涉及历史、哲学等他不那么“专业”的话题时,他似乎就显得有些故作高深,甚至语焉不详。这反过来也说明,布罗茨基最擅长的话题,说到底还是诗和诗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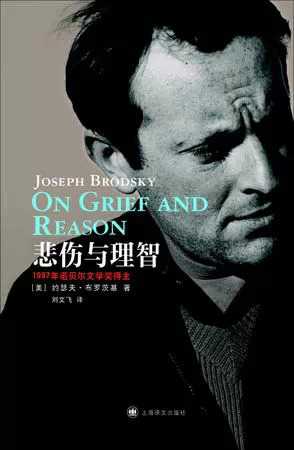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51:02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