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荐书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
>>>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 簡體 傳統 |
撰文:罗志田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再造文明之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去了解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个1891-1929年间的胡适。 这是一部关于胡适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独到的见识和洞察力,成就了这一经典之作。十年断版,第三次修订,这次不仅有罗志田先生为本书新写的序,交待了多年前写作本书时的“幕后”故事,还新添了一章“《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书写胡适在台湾的最后一段时光。 以下文字摘自全书第六章——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1917年3月,胡适将归国,在日记中记下了原出《伊利亚特》,而为19世纪牛津运动之领袖纽曼(Cardinal Newman)所常道的格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尚未归国,已有让人看到区别的意思,充分体现了经长期预备的胡适对自己将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觉。后来他更浅白也更谦和地将此语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在回国初年的演说中,也不止一次引用并曾以英文读之。实际上,胡适还未归国,已因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而先声夺人,区别已出现了。这一革命,不久就扩大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影响深远,已是非常“不同”了。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人之力,也不仅仅是归国留学生之力,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是相当突出的。对胡适来说,这就是他再造文明志业的起步了。本章就主要考察胡适在这一从文学到文化的运动中的努力和作用。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信然。关于文学革命,学界已研究得较多,但以胡适自己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的文学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唐先生也是先有―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并以此衡量胡适的文学观。但胡适的文学观确有不少“旁逸斜出”的特殊之处。在讨论文学革命的发动之前,先简单考察一下胡适在此前后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胡适自称他的文学观是“历史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是以进化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一般人都知道胡适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较少注意到他认为后一时代的文学通常胜过前一时代的。胡适说,在文学方面,“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胡适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看作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因此“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胡适一反大多数人认为宋诗不如唐诗的观点,认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不仅诗,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也不如宋人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还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 胡适也曾用他的进化文学观来解释西方文学史。他在论三百年来戏剧进步时说,莎士比亚只有在当日才可算算是“一代的圣手”,以今日的标言,“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胡适认为《奥赛罗》只是—部近代大家不做的“丑戏”。《哈姆雷特》也“实在看不出不出什么好处来”。胡的评判基础,就在于他对戏剧以至文学有—根本的衡量标准,即19世纪的写实主义(今译现实主义)。依此去看,以前的戏剧都不足论。不过,胡适的进化文学观又不是完全彻底的。他对西方后起的文学流派也不十分欣赏。据此,对民初中国那些以为写实主义已过时,说什么“今日的新文学应该谈‘新浪漫主义’了”的新人物,也只视为不可救药的“妄人”。这有可能是因他看不懂新派艺术作品:留学时曾看过—次,虽由韦莲司解释,终不甚了了;晚年仍说“大部分的抽象派和印象派的诗和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更可能是他认为中国的进化落后于西方,现在还没有到写实主义的阶段,当然也就不应率尔越级跳入“新浪漫主义”阶段。 这样的中西文学史观,不论在当时和现在,都要算是非常能“独辟蹊径”了。而有意识地“另辟蹊径”正是胡适文学史观的又一大特色。胡适曾把他自己也说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白话文学史视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这样一刀“截断众流”,置以前的文学于“边缘”地位,只有在进化文学史观武装下才有可能。但这还只是“竖断”,胡适还有更大胆的“横断”。他说,中国文学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文学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既然“旁行斜出”成了时代的代表,所有各具体时代处于边缘的文学家就摇身一变而成了“正宗”。简言之,胡适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先把所谓“古文传统史”划出去,再把历代的边缘文学串起来作为正统,然后据以否定历代文人自认的正统。这样的“竖断”和“横断”之后,一部新的文学史就出现了。可以看出,胡适治文学史的方法,实际是―种倒着放电影片然后重新剪辑的方法;以“另辟蹊径”的取向,集“旁行斜出”之大成。而其要点,就在于自说自话,根本不承认历代和当时的主流,当然也不与之对话。 前面说过,胡适先天有一股反叛气息。如果不是少年“暴得大名”,大约还要反得厉害。这样的性格使他特别不喜欢律诗、对联、骈文、八股以及写作中的用典。因为这些东西都最能体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中国传统,最不宜有反叛气质者。他常说律诗不通,一是要凑对子,一是要用典。胡适以为:“骈文、律诗,都是对对子;一直到八股,还是对对子。可见对对子是一条死路。”他觉得“律诗和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一旦摒弃过去的观赏标准,评判结果当然不一样。故胡适虽然背了几千遍杜甫的《秋兴八首》,“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他也认为苏东坡的文通诗不通,因其写诗好用典。胡适看了比他老一辈而享誉当代的律诗大家陈三立的《散原诗集》,发现里面“没有一首诗使我感动”。 不过胡适反对律诗和用典的文章,也因为其“故意叫人看不懂以没有文学的价值”。他以为,文学的价值就在明白清楚。“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胡适一向强调写诗作文不能只自己写,不管人家能否看懂。他说:“我的文章都是开门见山的”,而且胡适写文章的确是有心栽花。“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因为“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跟我一样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胡适有意想学梁启超,因为梁就能使读者跟着他走。胡适知道,要文章明白清楚就很可能会造成“浅显”,但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作文要“处处为读者着想”而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已体现出文字不过是工具的意思。 胡适文学观的又一个特点即是文以载道观念,这也是其不脱离中国传之处。至少到1915年夏,胡适对文学的理解基本是采文以载道的取向。他那时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为“甚不易读,其所写皆家庭及社会纤细琐事,至千二百页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终卷。此书所写俄国贵族社会之淫奢无耻,可谓铸鼎照奸”。小说而至于难读,足见胡适的认真。不过,如果托翁听见他的小说别人要靠耐心才能读完,岂不大愧。而胡适耐心读完之后,从书中所见却是“贵族社会之淫奢无耻”,颇类其读吴趼人、孟朴的谴责小说,这样的知音,大约也是要使托翁大摇其头的。—个月后他说,他在十六七岁时刊于《竞业旬报》之小说《真如岛》中,曾“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那就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观念。此时他已认为少年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则文学本身的优美也是重要价值。胡适虽然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少年时的局限性,但也许是因为少时的观念入其心中已深,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这一取向。 正是因为从文以载道的视角出发,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他自认明白清楚就是美)总喜欢以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其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将形式与内容分开,结果其讨论评判常常多及形式少及内容,有时甚至只及形式不及内容,给人以重形式轻内容的印象。前述他反对律诗骈文的,其实都在形式。胡适指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所以文学革命也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胡适一生治学,都有重视作为工具的“方法”超过工具所表达的内容这种倾向。这又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不一样了。中国传统的观念,文既然是载道的工具,当然远不如其所载之道重要(实际也确有不少人为了“因文见道”,结果只在手段上下功夫,始终未达“见道”的目的。但胡适却用他的进化文学观轻易化解了手段压倒目的这―矛盾,并以此作为他的文学革命论的一块基石。按胡适的意思,旧瓶是不能装新酒的,新酒必须用新瓶来装;瓶子如果不比酒重要,也至少与酒同样重要。所以,“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了解了这些观念,我们再来看胡适手创的文学革命,就较容易把握了。早在1914年夏胡适还没有自觉的文学革命念头时,他实际上已在开始文学革命了。前面说过,那年夏天他的思想一度动荡,此后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强,自觉“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体现在胡适―向自视颇高的做诗上,他已“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而且,胡适似乎特别喜欢做“吾国”所有的事。那年7月,胡适做了一首纯说理的诗,颇觉自豪。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远不如西人。我们且不管“言外之意”与“说理”之间有多少逻辑联系(实则恐怕根本是两事),但胡适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他的独创性。从方法到形式的“不依人蹊径”既然成为他做诗的一个发展方向,走向白话诗的可能性已见端倪,文学革命也之欲出了。 胡适自己把文学革开端定在1915年夏天他和一些留美学生开始着意于中国文字的改革。那正是在他转学前后,被停止奖学金,因中日交涉时的言论在留学生中很不得人心,又要转学,心情大约比较波动,容易兴奋和激动胡适自己解释所谓“逼上梁山”,即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那压迫他的“环境”,或者也就隐含这些扰人之事。有位姓钟的留学生监督处职员,每在给学生寄支票时夹寄一些受传教士影响的文字宣传改革。胡适以前收到无数次,并不觉十分反感。但此时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在又收到关于中文应改用拼音的宣传文字时,一向颇有修养的他竞写信去骂钟某。寄信后又有些后悔,于是他约赵元任共同在美东中国同学会上发起了一个文字改革的小组讨论。 但胡适所谓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主要还是“由于我个人的历史观念很重,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结果却做出许多激进的事。这话中的“经常”二字尤其准确。因为胡适虽然不时“率性”,主要还是向往着“作圣”。而且,就对中国文字的态度言,胡适在那时确实属于偏保守的一边。那时在美国,“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胡适则认为:“吾国文字本可运用自如。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inflexible),徒见其不通文耳”。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胡适自己有少年时的特殊训练,对中文运用颇能自如。而有些留学生不仅不通中文,甚而不会中文,看法当然不―样。中国的文字是胡适一生中一直公开肯定的少数中国事物之一,他后来多次言及中国文字的长处,包括在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时也是如此。而且,在那次文字讨论会上,赵元任的题目是汉语拼音化,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文言易于教授。从题目看,胡比赵还稳健保守得多。足见胡适在那时确不算最激进者。 实际上,胡适那时的有些观念还基本在传统之中。194年他参观波士顿图书馆,见“藏书既少,而尤鲜佳者,《三国演义》《古今奇观》《大红袍》等书皆在焉”。在中国旧小说中,《三国》的确不是胡适最欣赏者,但后来逐渐“激进”起来时,也曾把《三国》捧得很高。此时却作为藏书不佳的例证,正是典型的士大夫观念。而且,胡适在留学时所做日记及其他文字仍用古文。他二十岁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现在看起那个调子来觉得有点难为情。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这是晚年倒放电影时才觉得“难为情”,当时却不然。他写该传的结论部分,不过三百余字,竟“终日始成”,不禁慨叹“久矣余之不亲古文,宜其艰如是也,”则知虽因久不做古文而笔已生疏,口气还是亲切的。值得一提的是,林译小说一般要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才较多被人用为古文范本(详后),胡适真要算林纾少见的知音了。 前面说过,胡适的防守心态甚强,每遇压力,必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外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他自己所说,“一连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渐的强迫我采取了”激进的立场。这些外在因素当然也不都是压力,比如胡适提到的“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就是康乃尔附近来了一个中国女学生陈衡哲。陈女士触动胡适的,也许不及她触动后来的夫君任鸿隽的多(至少从被触动动者的一面是如此)。胡适在离开康大到哥大时,先以“我诗君文两无敌”与任鸿隽划分了文学领域的“势力范围”。可是—向被胡适视为忠厚的任鸿隽,在与胡适辩论诗的形式时一直不让步,多少有在陈女士面前争胜的心理在起作用。任鸿隽暗示胡适的诗言之无文。他说,中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所以,解救的办法在加强学问而不是在文学形式上做文章。他特别指出:“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忠厚的任氏尚且不让步甚而进攻,当然更促进了胡适的“斗志”。 关于胡适与其朋友就文学革命的辩论内容,几乎每一本有关胡适的书都所述甚详。3本书就不必重复了。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胡适认为可以用作文的方法做诗;因古文已成“死文字”,故可可以用白话入诗,进而到完全用白话做诗。双方辩论不休,“愈辩则牵涉愈多。我的朋友们愈辩愈保守;我也就愈辩愈激进了”。可知辩论双可知辩论双方,可能都有为取胜而强化立场的倾向。如胡适最强硬的对手、因辩论而几至绝交的梅光迪所说:足下“自居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不过,大体是胡适“激进化”的程度超过他的朋友们“保守化”的程度。实际上,梅氏就并不反对文学革命,他自己在这封信中就也提出四项大纲作为他的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 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的诗中,有广为为引用的几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这里胡适第一次点出了“文学革命”四字。但胡适这里要“鞭笞驱除”的鬼是中国的鬼,可是任鸿隽戏和其诗,挖挖苦胡适的“文学革命”不过就是将外国人名音译入诗;并将并将这些音译字集在一起,也说是“鞭笞一车鬼”,但特别注明此鬼乃“洋鬼子之鬼”,意思遂一大转。胡适似乎并未读出他和任鸿隽两人取向的差异,这是他将要走上反传统统路径的先声,只是还没有到“有意”的层面。但胡适知道任是在挖苦他。他虽强作不知其究竟是“知我乎?罪我乎?”终于还是觉得要讲清楚,所以在和在和诗中一面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一面希望大家“愿共努力莫相笑”。 此后,胡适在颇感“孤独”的心境下,努力以“作诗如作文”的方式创作白话诗,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诗国革命”。他先定下了《尝试集》的题目,然后进行他的尝试,可知也还有相当的自信。胡适本自认是留美学生中做诗的第一把手,也常有同学称赞他,如留学生张子高就说胡适的诗文足以当“雅洁”二字。胡适自己则说“吾诗清顺达意而已”。此话看来颇为谦虚,但如果对比前引胡适所说清楚明白就是有力量,有力量才是美的观念,这已是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他在1916年初总结自己去国以来的成绩,觉得散文虽“有退无进”,韵文则“颇有进境”。这大约是他后来把作文的头把交椅让给了任鸿隽的原因。胡胡适到晚年看法依旧,认为他留学时的“文不如诗,诗已有了家数,能够达意,不用典了”。 以今日对诗的看法而论,胡适以作文之法做诗这个“尝试”,并不十分成功。曾受胡适攻击的南社诗人柳亚子就说胡适“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柳或不免有反唇相讥之意,但诗与文如果全无区别,则何必写诗?一般而言,诗在宣泄感情上的功能似大与其表述观念的功能,而胡适做诗恰好反是。周策纵先生说,胡适的“个性太冷静、太‘世故’了……所以他的诗、文,都有点冷清感,与梁任公常带感情的笔端大不相同”。比如,胡适哭亡女的诗就“写得太做作,太轻浮,太不能动人感情了”。又如,“丁文江和徐志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们的诗,也都没有热情流露感人之处。”特别是写徐志摩那首,“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够深沉厚重”。更要紧的是,胡适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所为而作,有意见要发表,就是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周先生的见解是有见地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当胡适的诗确由“情感冲激而成”时,也是相当能“以情移人”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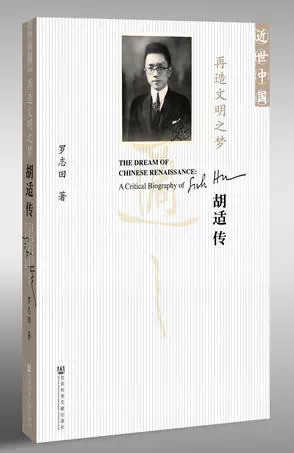
东方历史评论 罗志田 2015-08-23 08:50:1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