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周六荐书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
>>>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 簡體 傳統 |
撰文:蒂莫西·加顿艾什 翻译:于金权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穿行于真话讲述者和政治骗子之间,以手术刀般锐利的笔锋记录下他所发现的真相。他的《事实即颠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收集了自新千年开始以来所写的政论文章,所论的都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忍受长期独裁的人民,当他们起而建立民主国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推翻暴政的自由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在具有不同信仰和种族的社会中贯彻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权利平等,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们选摘该书的导读和第一章节部分内容,与你分享。 导读:老英国自由派的犹豫 撰文:梁文道 一 据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这句话简单直接,似乎大家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甚至还能同意。但只要稍稍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其实问题重重。例如,它似乎隐含了一个标准,一个什么事情能被写进历史的标准;难道只有今天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事实才够得上历史的殿堂吗?当然不,因为我们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在判断什么事情才有新闻价值的时候,总是已经先有了一套预设,而这个预设又总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明天的史学家凭什么要全盘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呢?此所以重大的史学进展往往和新史料的发掘相关;那并不只是新发现了一批被人遗忘的文档那么简单,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从未想过要入档留存的东西当成史料。比方说树木的年轮,前人可曾觉得这是诉说他们那个时代事实的重要线索吗?可今天的史家已能学会在一片树林的年轮里判读过去气候变化的痕迹,从而掌握往昔人们生活劳作背后的自然条件。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说,今天的新闻固然可以是未来的历史,但对今日新闻标准的疑问更有可能是未来历史学者的重点。 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只是事实如何发掘,更是事实到底可以证明什么的问题。自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种忽略事实与证明之关系,转而强调事实被诠释被叙述的倾向(或者可以叫做后现代倾向),就渐渐又变成史学主流的趋势了。因为什么算是史料,什么叫做事实,基本上是个看你把它们放在什么框架之下叙说,又如何叙说它们的问题。毕竟,任何时代的人用以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视界及价值标准,都是一些可以说出来的叙事,并且还可以不断重新叙说。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讲“故事”、“叙述”和“书写”乃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几乎恨不得把历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说似的纯粹叙述技艺。相反,依旧坚守某种单纯甚至天真的事实之力量,则是不合时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实即颠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书,因为它连书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书序言里所讲的,他依然相信“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这是真的吗?事实本身就具有这样的颠覆性吗?还是说编纂事实和安排事实的新叙事使得事实颠覆? 加顿艾什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过英国《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后来在《卫报》有固定的专栏,而且还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曾经长年住在东德、波兰和捷克,跟哈维尔与瓦文萨变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认为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身边的顾问,穿梭于学院、政坛和大众媒体之间,其着作读者不计其数。老和他笔战的新左派史学大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带着贬义地)说他是冷战末期推倒东欧共产政权最有力的一个声音。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才译出了他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读者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可我还是长年阅读他的着述。且引一句当今左派大红人齐泽克的话:“尽管他是我的政治对手,我也一直认为他那些丰富的精确观察仍是值得阅读的,可以作为东欧沧桑剧变的可靠材料来源。”的确,整个英语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东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本行领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动人的着作《档案》(The File)当中,他回到德国翻查公开了的斯塔西档案,发现不少当年圈子中的朋友原来都是秘密警察的线人,曾向当局报告他这个英国人的言行和心理,这个发现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满阴郁气氛的溯往旅程,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情谊的脆弱与极权社会最深处的秘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外国人都会有的;就算有,也不会有他那种专业史学训练所赋予的识见和涵养,好把这个经历写成一部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分量十足的深度回忆。 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作比。布鲁玛的对象是日本和东亚,而加顿艾什则可说是东欧的布鲁玛。他俩都是记者型的学者,或者反过来说是学者型的记者。从奥威尔开始,记者就已经取代了那种会渲染异国风情和浪漫化自身经验的传统外游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从未去过的曼德勒写成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比较可靠也比传统学者有趣的外国知识来源。所以当前市面上介绍各国情况的非虚构书籍当中,那些驻外记者的作品总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晓得怎样和公众读者沟通,又有长年的第一手经验,有的甚至还具备了相当不错的学养。加顿艾什和布鲁玛就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是20世纪后期大众传媒国际化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有点像人类学家,在祖家和他乡之间迂回,因此往往能在一段距离中清醒观察本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另一个框架之中考察省视。当然,加顿艾什同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德国史的了解要比许多德国百姓厚实得多,于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时候就有了一道从往昔深处照下来的微光。 然而,《事实即颠覆》并非典型的加顿艾什。因为东欧在他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写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缅甸,甚至香港。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凭什么去写那些他没有长住过的土地?又凭什么去和当地人沟通(访谈是记者获得事实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晓当地语言一向是学者型记者的基本要求。加顿艾什会波兰文、捷克文与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吗)?他甚至从来不是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他怎能写那么多关于欧洲穆斯林的评论呢?当所有通向事实的管道都不是那么扎实,当事实本身都难以获致的时候,事实还可能有颠覆的力量吗? 二 虽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教书,是个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学院里的理论发展似乎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不会像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那样,在史学方法论上细致探讨事实、证明与修辞的关系。他用心的事实问题,是种更接近新闻记者专业关怀,更贴近常识意义,或许因此也更容易为人理解—同时也更容易犯错—的问题。比如在谈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拥有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当成事实。结果呢?他自然错了。在整个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个不好笑的笑话一样。不只如此,加顿艾什在那篇文章里头竟还说道:“萨达姆政权是当今世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之一。他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还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推翻他对他的国家和该地区而言都是福音。无论战后的伊拉克会多么混乱—肯定会混乱,就像战后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样—它几乎已经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实却颠覆了他当年的判断,这大概是所有时事评论家的尴尬。 《事实即颠覆》原书出版于2009年,加顿艾什本来有机会删掉这篇他自己都很后悔当时弄错了事实的分析;可他没有。一来,就像他所讲的,错了就是错了,不掩过乃是道德义务。二来,我猜让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饰地在那篇文章题目里头就已经表达出来的态度;它叫做“为骑墙派辩护”。也就是说,尽管他相信“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是个事实,相信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的伊拉克一定会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轻言美国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反战派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也很说得过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不要忘记,那可是个黑白多么分明的时刻。布什声称:“你要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他们那边。”中国则有人一边看着电视里的世贸大楼倒塌一边拍手叫好,同时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署宣布“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战或不战,义或不义,几乎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而加顿艾什居然要为骑墙派辩护?没有立场?那你写这篇东西干什么?他的解释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热情洋溢,过分简单地相信复杂的两难处境中的一面,即使这样确实可以让电视更好看。”他甚至认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态度:“我的直觉是,如果你在黑夜中为托尼·布莱尔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将基本上坦承这种自由派的犹豫不决。”“自由派”,就是这里头的关键词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像时下中国许多施密特及施特劳斯的信徒所以为的那样,是批没有价值倾向的虚无论者。最起码,自由主义者要相信言论的自由。好比加顿艾什,他可以同情欧洲穆斯林的处境,但他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信仰受到冒犯,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跑去杀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画家。而且他还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主张“所有神明的信奉者与那些坚持没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广场上试一试”;所以他比较不赞成法式启蒙运动的路子,干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头罩还是十字架项链—出现在广场之上。这样的自由派会拥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当年他要和哈维尔等东欧异见分子站在一起,主张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派还会看重一些最显眼的事实矛盾,不屑于理会对那些矛盾的各种深奥辩解,所以他要说前东德禁止了自己国歌的歌词(因为它歌颂“统一的德国”),是对自己覆灭的恐惧(因为它害怕会被西德统一)。我们知道,除了前苏联和前东德,这世上还真有些政权害怕人民过度认真对待国歌与执政党的党歌,而且居然有人辩说那是“复杂国情与时代的错位,不能简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加顿艾什这种自由派看来,你担心人民把国歌当真,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问题,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烦不是价值虚无,而是对付不了种种身份认同困扰背后的激情。在英国人算不算是欧洲人这个大题目上,懂得欧洲并且亲近欧洲的加顿艾什分析过其中各个应该考虑的条件之后,再度摆出了骑墙的态度:“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还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身份认同也好,政治立场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确的结论,可加顿艾什这种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却只能提供倾向。他欢迎前波兰和前捷克政权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个转型的困难。所以他当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当成神只来朝拜的人那样,不顾现实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愤慨现实的人,走上怀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国家主义的道路。像加顿艾什这般的自由主义者,总是要在信念支撑的理想倾向与层出不穷且困扰理想的事实之间,进退犹豫。 由于《事实即颠覆》离开了加顿艾什熟悉的安全地带,因此他在这部文集里头变得更像那些什么国家的事都能够畅谈一番的“国际问题专家”,这部书于是就更能考验他身为记者、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能耐了。又由于他在事实材料的拥占上不具优势,所以带动他写作的信念和倾向就会变得更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战。他是个记者,把自己的写作类型规定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误会,这不是福柯所说的那种“现在如何成为现在的历史”,而是冷战“围堵理论之父”乔治·凯南推介的学术与新闻的混合写作),所以他当然要发掘事实,最大程度地亲近现场。但他究竟是个历史学家,就算不爱谈太过哲学化的史学方法论,却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从现场带回来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期间,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灯剧院一间奇特的玻璃墙房间里会面,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一本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记得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历史一样,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记忆问题就是见证人问题的核心所在……记忆是一个可以重新加工的CD,会受到不断地加工,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让我们感到更加舒服。 历史学家加顿艾什疑虑的,大抵就是这种舒服,把事实裁剪修整得较为合体,较为符应论点逻辑的舒服。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所疑虑的,则是让自己皈依某个既定立场的舒服。他宁愿让理想和倾向不停在现实上头对焦,找不着安稳的落脚之处;他宁愿让现实持续地发出噪音,扰动理想世界的安宁。所以他总在犹豫、进退。在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或许就是这本书值得当今国人一读的理由。 第一章 天鹅绒革命,绵延不绝 米洛舍维奇的奇怪倒台 2000年10月5日,星期四,塞尔维亚人冲进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议会大楼,从燃烧着的窗户中挥舞着旗帜,并占领了国家电视台的总部(有一位反对派领导人曾经将它们称为“电视巴士底狱”),这看起来像是一场真正的旧式欧洲革命。攻打冬宫!攻陷巴士底狱!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终结后继续掌权的最后东欧统治者、“巴尔干屠夫”会步上所有暴君的后尘。有激动人心的报道称,三架飞机正在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家人送出国。也有报道称他像希特勒一样躲在地下掩体中。他会被私刑处死吗?会像齐奥塞斯库一样被处死?还是会像他的父母一样自杀?“拯救塞尔维亚,”人群喊道,“自杀吧,斯洛博丹。”革命的形象以及“巴尔干半岛人”让人联想到的所有血腥场面,引来了数百名记者,前来报道这一可怕却适合上镜的结局。 出人意料的是,10月6日,星期五晚上夜深的时候,米洛舍维奇出现在另一个国家电视台上,发表了和善的败选演讲。人们觉得美国总统或者英国首相才会发表这样的演讲。他说,他刚刚收到消息,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štunica)赢得了总统大选。(这话竟然出自他之口,过去11天,他一直在努力通过选举舞弊、恐吓以及操纵法庭来否认这一点。)他感谢了那些选他的人,同时也感谢了那些没有选他的人。现在,他打算“多陪陪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孙子马尔科”。随后,他希望重建其社会党,使它成为反对党。“我祝贺科什图尼察先生获得胜利,”他总结道,“我祝愿南斯拉夫的所有公民在今后几年取得成功。” 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整洁的西服、白衬衫,打着领带,但却僵硬地站在南斯拉夫国旗的旁边,双手交叉着,在身前放得很低,像一个作弊被抓的男学生一样,或者说像在牧师前忏悔的人(他的父亲曾经希望当牧师)。对不起,神父,我在选举中作弊了,毁掉了我的国家,带给了邻国无尽的杀戮和痛苦,但是从现在起我将做一个好人。假装这只是一次普通又民主的领导人换届,既不协调又离奇可笑。 然而,这也正是新总统希望假装的。科什图尼察总统后来告诉我,米洛舍维奇曾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发表演讲,他很高兴,因为他希望让塞尔维亚的所有人知道,权力的民主和平交接是可能的。同一天晚上早些时候,科什图尼察曾出现在“解放”的国家电视台上,一如既往地穿着得体且严肃,回答公众的电话提问,镇定自如地谈论投票制度,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没错,当晚,我发现有年轻人在议会大楼前吹哨跳舞庆祝。但是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朋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人—既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也没有表现出愤怒不已,而是在情不自禁的喜悦中略感疑惑。他真的完蛋了吗?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很明白。见鬼,这不应该是一场革命吗?但这场革命似乎始于星期四晚上,而星期五早上就结束了。不再有壮观的场面。没有流血事件。塞尔维亚人没有引发流血事件。他们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失望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更会配合。他们正在互相拼杀。因此,第二天,一半摄影组奔向了以色列。那些留下来的人还在继续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这算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同日早上,科什图尼察搬进了有回声的联邦宫(Federation Palace),就在接待俄罗斯外长前几分钟,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叛乱中的传奇老兵“德拉甘上校”(Captain Dragan)在他的手臂下面别着一把天蝎式自动武器,带着一队武装人员向联邦海关大楼走来。他去那儿是为了将米哈利·科特斯(Mihalj Kertes)驱逐出境,米哈利·科特斯是米洛舍维奇的亲信,通过海关控制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德拉甘上校告诉我,科特斯在颤抖,苦苦哀求饶他不死。 星期六,科什图尼察不得不在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萨瓦中心的简陋接待室里站了几个小时,等待反对党和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新当选的议员解决他们的分歧,让他按照宪法正式宣誓就职。与此同时,一队“红色贝雷帽”国家安全特种突击队,包括参加过武科瓦尔(Vukovar)和科索沃(Kosovo)行动的塞尔维亚老兵,正在占领内政部。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反对米洛舍维奇,或者说至少部分原因是如此。 在政党会面共同讨论新联邦政府之际,工厂和办公室内自封的“危机委员会”以人民的名义解雇了他们先前的老板。前一分钟,我还在看准军事部队领导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在塞尔维亚议会的会议上谴责这场革命。接下来,我就在仔细观察德拉甘上校从可恨的科特斯那里拿过来的手枪了。那把手枪相当轻便,紫檀木的枪托上刻有花纹,相当漂亮,里面有五发软头子弹和一发普通子弹。 然而,米洛舍维奇一直静静地坐在德丁杰(Dedinje)郊区郁郁葱葱的山间别墅中,与他的旧党在一起商讨。在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天,我开车经过尤兹克卡(Užicka)大街上的这些房子,它们躲在高墙和防护篱笆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连门铃都无法找到。 一 这场塞尔维亚革命是什么?显然,有关塞尔维亚事件的许多事情尚不明朗,但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会被跟波兰1980—1981年间“自我约束”的革命和1989年欧洲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evolution)进行比较。我最初的解读是,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一切是一个独一无二又错综复杂的组合体,由四个要素组成:有点儿民主的选举、自我约束的新天鹅绒革命、较古老的短暂革命政变和些许旧式的巴尔干阴谋。 首先是选举。许多外界人士不知道的是,与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不同,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从来不是一个极权国家。这是他倒台与众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没错,他是一个战争犯,给前南斯拉夫中塞尔维亚的邻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在国内,他不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统治者。相反,他的政权是民主和独裁的奇怪混合体:民主专制国家。 在米洛舍维奇的统治下,党派斗争不断,多个党派互相斗争。连执政党也有两个:他自己和他妻子各自所属的政党。他自己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塞尔维亚社会党与妻子的南斯拉夫左翼联盟(Yugoslav United Left)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他的权力根基动摇。但是如今即将掌权的反对党和反对派政客,包括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也已经参政十年了。没错,是有警察及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甚至还包括政治暗杀,但是也有选举,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中获胜了。 它们不是自由公平的选举。他的政权最重要的单一支柱是国家电视台,被用来维持民族主义的受困心理,在居住于没有什么其他信息来源的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们中间尤其是如此。因此,他最早的政治对手之一,武克·德拉什科维奇(Vuk Draškovi)称之为电视巴士底狱。但是也有设防的独立广播电台和私营报纸。人们可以旅行,几乎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可以上街游行。反对党可以组织活动和竞选,在议会和市议会中也有他们的代表。米洛舍维奇掌权的另一种方法是在他们中间巧妙周旋,分而治之。比如,上面提到的德拉斯科维奇受命接管了贝尔格莱德市政府,人们都说他同时也接收了随之而来的致富源泉。 在这个贫穷、目前深陷腐败的国家,钱财在政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所指的钱财是指塞在黑色皮夹克口袋里或装在手提箱里带出国的大量德国马克。政界、商界和有组织犯罪机构之间的边界完全消失了。米洛舍维奇的可恶儿子马尔科是一名商人,同时也是个强盗。他有众多家产,其中一家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香水店叫斯康达(Skandal),这个名字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译按:谐音scandal,意为“丑闻”)。10月6日,星期五晚,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起注视着这家被洗劫一空、烧焦的店。他带着米洛舍维奇的孙子马尔科逃到了莫斯科。 从黑手党的角度来理解,执政的家庭是更大家庭的核心。然而,这位“教父”还在表面上保留了宪法的形式,定期在选举中寻求连任。他获胜得益于电视巴士底狱和有些悄无声息的投票舞弊,还因为他可以利用四分五裂的反对派,依靠真正相当高的支持率。 只有知道这些背景,才能理解为何7月初米洛舍维奇决定修改宪法,寻求直接连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但当初,这样认为的人寥寥无几。 他自己呼吁在9月24日进行选举,为什么他会在选举中败北?最首要也最温暖人心的部分答案无疑是:动员其他塞尔维亚人击败他。在“塞尔维亚人”都被妖魔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他们”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所作所为,人们常常无法坚定地说总是还有其他塞尔维亚人。一开始就有塞尔维亚人发表演说、写文章和组织活动来反对米洛舍维奇。他们的斗争与在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异见分子的斗争不同,但难度或者危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的异见分子冒着被克格勃(KGB)逮捕入狱的危险。塞尔维亚的异见分子冒着在漆黑的小巷中被陌生的暗杀者枪杀的危险。他们人数不多,但总是有这么一些人。 韦兰·马蒂奇(Veran Mati)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身材粗壮,留着大黑胡子,性格沉着冷静。你总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他在一台轻巧的手提电脑上打字。马蒂奇有一个敬业的记者团,又有西方的大量金融资助,于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广播电台—B92电台,科索沃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当局控制了这个电台,但它仍然在网上提供新闻。他还开办了一个叫ANEM的网站,为不受米洛舍维奇控制的省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提供独立的新闻和时事节目。目前,“电视巴士底狱”谴责科什图尼察和反对派是北约的走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但该网站却泰然自若地告知贝尔格莱德外面的人这场竞选活动的真相。此外,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记者因为报道他们自认为是真相的东西锒铛入狱。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名为“奥特波尔”(Otpor)—意为“抵抗”—的学生运动。它成立于1998年,与1996年和1997年的抗议一脉相承,但更加激进。一名活动人士告诉我,在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研讨会上,奥特波尔的成员学习了其他地方的权力运动和非暴力反抗是如何组织的,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到去年在克罗地亚的活动。这些都是“比较革命”专业的学生。但是他们自己添加了很多种创新的变化。比如,他们会穿着上面有“塞尔维亚的一切都不错”字样的T恤,出现在购买糖和石油的长队中。他们举着画着紧握拳头图案的独特横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警察。在革命爆发前的一年里,有1 500多名奥特波尔的活动分子被捕。 在1998年的斯洛伐克选举中,民间团体的活动分子推翻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Vladimir Meiar),与此一样,他们组织了运动来“摇动投票”。流行的摇滚音乐会与出去投票的信息相结合。他们设计了一个口号,“Vreme je!”,即“时机已到!”或“现在是时候了!”,而这恰恰是1989年人们在布拉格所喊的口号。随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口号,“Gotov je!”,即“他完蛋了!”,作为这场革命的名言,涂在米洛舍维奇的海报上,写在帽子和横幅上,涂在这座城市的墙壁上,还被十万人喊着。 在这个独立活动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人—在斯洛伐克,他们被称为“第三部门”—致力于该事业。独立的民意调查者(其中一些人由美国资助)会定期作调查,调查表明科什图尼察正在取得胜利。竞选志愿者和独立的选举监督人员数不胜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欧洲,西方在“民间团体”项目上浪费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次,在这里,确实是物有所值了。 其次是意见迥异的反对党最终团结起来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反对党。最大的反对党,即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党(Serbian Renewal Movement),拒绝加入。此外,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Djukanovi)呼吁抵制选举,因而让米洛舍维奇实际上拿到了所有留下来的黑山人的选票。但是还是有十八个党一起加入了塞尔维亚民主反对党(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其中最大的党是民主党,该党党首是反对派领导人佐兰·金吉奇(Zoran Djindji),他任职很久了,但容易妥协,不得人心。 米洛舍维奇败北的第三个原因是,金吉奇和其他人彻底平息了他们内部的争执,一致提名让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当候选人。科什图尼察是小塞尔维亚民主党的领袖,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民主党分离出来。科什图尼察不太愿意去竞选—他自嘲道,自己是第一位犹豫不决的选民,但这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为他集四种品质—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不腐败和迟钝—于一身,独一无二。 科什图尼察从来都不属于共产党。他是一名宪法律师和政治学家,1970年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反对党在多党制中的作用。他后来翻译了《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还专门研究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洛克(Locke)。由于反对铁托(Tito)1974年颁布的宪法,称该宪法对塞尔维亚人不公平,他被贝尔格莱德大学开除。与大多数其他反对党领导人不同,他竟然从未见过米洛舍维奇,直到10月6号,星期五,军队总司令内博伊沙·帕夫科维奇(Nebojsa Pavkovi)才给即将离任和上任的总统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会面。科什图尼察自豪地告诉我:“因此我是在他垮台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他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曾支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强烈批评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战争。与德拉斯科维奇和金吉奇不同,人们从未看到他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过从甚密。轰炸期间,他一直留在贝尔格莱德,而金吉奇逃到了黑山,或许正是担心自己的小命不保。 他不腐败。我基本上还未见过比他的党务办公室还简陋的办公室。他和妻子还有两只猫一起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开的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南斯拉夫牌汽车。这又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尤其是金吉奇和德拉斯科维奇)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穿着光鲜亮丽的西服,开着快车,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贪污腐败。在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世界里,大多数政客都是这样做的,由来已久。 他的一大劣势是他的迟钝。不过在这件事上,连迟钝也是一项优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他们喜欢他慢条斯理、行动迟钝的风格。他们说,迟钝非常受欢迎,与米洛舍维奇悲壮的装模作样和他的许多对手,比如说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夸夸其谈形成对比。一位首席独立记者告诉我:“你懂的,我想要一位乏味的总统,还想生活在一个乏味的国家里。” 话说回来,毕竟科什图尼察也没有那么迟钝。他发现自己成为祖国解放运动的领袖,备受鼓舞(谁会不受鼓舞呢),于是带来了一些英勇无畏又令人难忘的时刻。他在议会和电视台被占领的那天晚上所说的“晚上好,解放的塞尔维亚”将载入史册。 9月24日,星期日,至少有240万塞尔维亚人在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圆圈。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让他们这样做的所有动机,但是有人给我提供了两个引人注目的部分解释。 一个解释与北约的轰炸有关。我问政客和分析人士,他们认为革命是何时开始的。有几个人表示,常常撅着嘴说:嗯,老实说,科索沃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一结束后,都在国旗下举行过爱国集会,米洛舍维奇也从中受益。但是这也太荒唐,太“奥威尔”(Orwellian)了,国家电视台竟然声称这个历史性的明显战败是一次胜利:塞尔维亚的耶路撒冷—科索沃—输得其所。在经济方面,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在轰炸的影响下,每一项勒紧裤腰带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科卢巴拉煤矿的矿工—他们的罢工对这场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告诉我,战后他们的工资从平均每月150德国马克降到了70德国马克的低位。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为战后重建交税。但这让他们怒不可遏。 正如韦兰·马蒂奇所说,当时米洛舍维奇“竞选不是为了对抗我们,而是为了对抗北约”。然而,这没有起作用,因为人们内心更深处认为:“不过,他对抗北约输了,不是吗?”如果马蒂奇说得对,那么科什图尼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所谴责的轰炸的受益人。当然,这种解释疑点重重,永远无法证实。但战争推波助澜引发革命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另一种部分解释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也令人信服,至关重要。那就是许多过去选米洛舍维奇的人只是觉得受够了而已。这位领导人脱离了现实。他执政这么久,应该为当前的苦难负责。变革的时候到了。奥格年·普林彼斯维奇(Ognjen Pribievi)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米洛舍维奇,他说,这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分别掌权十一年和十六年之后发生的一切一样。与撒切尔或科尔作比较可能令人吃惊,甚至显得无礼。但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提醒我们,对于许多塞尔维亚的选民来说,米洛舍维奇不是一个战争犯也不是一个暴君。他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坏事,但是现在必须下台了。 正是这些人最终选了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让他的票数超过了50%,在第一轮中当选。 这场选举就是那样。在9月24号,星期日晚上,一个成熟又独立的选举监督组织—外国资助的“第三部门”的一部分—告诉反对派,科什图尼察已经获胜,人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一直狂欢到凌晨。但所有人都知道,米洛舍维奇不会认输。他可能试图“偷走这场选举”,声称从黑山和科索沃获得了额外的选票,来欺骗人们。好戏才刚刚开始。 可以肯定的是,米洛舍维奇让联邦选举委员会宣布科什图尼察获得票数比他多,但不足以在第一轮中胜出。必须要在10月8号举行第二轮选举。反对派当时没有听从许多西方政客和支持者的建议,豪赌了一把。他们表示:不行,我们不会进行第二轮选举。相反,通过策划和平的大众抗议,他们将迫使米洛舍维奇承认他在选举中败北。他们还设定了截止时间:10月5号,星期四下午3点。 这场竞选运动已经带有革命动员的性质,与1989年夏季在波兰团结工会发起的竞选运动如出一辙。这就是所谓的反思。但是目前形势更加明确地朝着新风格的和平革命发展。人们走上贝尔格莱德以及其他城镇的大街举行大游行。反对派知道这样还不够。毕竟,1996—1997年的那个冬天,米洛舍维奇挺过了三个月的大游行。因此他们呼吁进行全面罢工。他们呼吁塞尔维亚的所有公民在10月5日星期四那天来贝尔格莱德游行,结束所有的游行。 全面罢工一开始非常零散,但在一个重要的地方站稳了脚跟:科卢巴拉的巨大露天煤矿场,大概在贝尔格莱德向南三十英里的地方,该煤矿场提供的燃料发出了塞尔维亚一半以上的电。它不可避免地被比作了格但斯克(Gdańsk)的列宁造船厂—1980年波兰革命的发源地。探访科卢巴拉的矿井确实感觉回到了二十年前波兰的矿井和造船厂。同样的塑料桌子、盆栽植物、透孔的窗帘、无数的茶杯,还有一台旧收音机中传出的民乐。工人们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留着胡子,脸上脏兮兮的,带着失而复得的尊严。 与那里一样,在这里,共产主义工业化的一大堡垒—此刻大约有17 500人受雇在科卢巴拉的基地工作—最终向其制造者倒戈。同样,在这里,更加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与民主反对党有关系,是革命的半导体。像三十六岁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卡里卡自称是科卢巴拉的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他说:“但有许多莱赫·瓦文萨,我们都是莱赫·瓦文萨。”卡里卡坐在咖啡厅里,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戴着一顶鲜橙色的棒球帽,喊着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英雄的口号:1+1=2。一个选举监管组织把他挑了出来。卡里卡透露说,他最喜欢的流行歌曲非常红,是由着名的南斯拉夫乐队阿兹拉(Azra)演唱的,庆祝的是1980年格但斯克罢工。 与在格但斯克一样,经济问题推波助澜,引发了这场罢工,但工人立即牺牲了他们当地和物质上的需求来满足全国和政治的需求。当军队总司令帕夫科维奇和与他随行的政府部长答应如果他们复工便给矿工增加一倍工资时,他们坚持只要一样东西:认可选举结果。罢工工人也有团结,但力度不够。10月3日至4日的晚上,煤矿场罢工的工人减少了,警方入驻了。因此罢工的领导者呼吁人们前来支持他们。附近的拉扎雷瓦茨镇和首都来了数千人。在一个矿井外面,警察警戒着,但有些踌躇。最终,三位老人开着一辆拖拉机,缓缓朝他们开去,警方的警戒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这要么是电影里的场景,要么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刻。 不应该夸大与格但斯克的相似性,我可以说出许多不同点。但是科卢巴拉的罢工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它增强了革命的势头,进一步破除了恐惧的壁垒。随之而来的完全是塞尔维亚人。 10月5日,星期四凌晨,许多汽车和卡车车队纷纷从省城、查查克(Čačak)和乌日策(Užice),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和瓦列沃(Valjevo)出发,还有从位于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肥沃平原和位于南部的塞尔维亚中心地带舒马迪亚(Šumadija)出发。来自查查克的车队由长期担任市长的反对党人韦利米尔·伊利奇(Velimir Ilić)领导。该车队有一辆铲车、一辆重型推土机和一些重型卡车,上面装着大石块、电锯,没错,还有枪。他们差不多将强行堵在路上的警车推到了一边。其他车队也通过谈判和武力打破了警方的封锁。 许多赶到贝尔格莱德的人都是来自反对党控制的城市的普通民众,由于当地有独立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有时他们收到的信息要比住在首都的民众多,但是生活常常没有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人好,因此更加愤怒。然而,在他们当中也有当过警察和士兵的,还有参加过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的老兵。他们表情坚毅,光着头,皮夹克下面夹着枪。他们知道如何战斗,决定取得那天的胜利。 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贝尔格莱德,加入了成千上万贝尔格莱德人的游行大军中。宪法法院最近作出了荒唐又富有挑衅性的裁决—宣布这场总统选举无效,这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因此,他们聚在一起,举着国旗,吹着哨子,拿着写有“他完蛋了”的横幅,站在壮观的议会大楼(联邦选举委员会伪造了选举结果,它的总部也在这里)前。 3点钟了—这是这场革命的截止时间。接着过了3点,人群中就有人对扎克·科拉奇(Žarko Korać)(他是反对派的领导成员,设定了该截止时间)说:“哦,教授,已经7点多了……”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这样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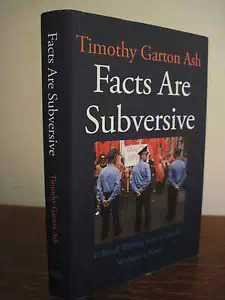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9:3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