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专题 吴飞:自杀问题再反思
 |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 簡體 傳統 |
我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的跋中曾经谈到,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可以算作我的文化反思工作的一个开端。而从《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完成之后,我已经结束了针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因为我觉得我应该通过其他问题来深入自己的文化反思。虽然不时有各界的朋友问我相关的问题,希望我能继续研究其他类型或其他地区的自杀现象,我都婉拒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不再认为自杀是个重要问题,而是因为我并不想成为研究自杀问题的专家。自杀问题虽然很重要,但它毕竟只是观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角度而已,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问题上。这次承《开放时代》吴铭先生的邀请,我读了该刊准备发表的一组三篇研究自杀问题的论文,并答应写一篇相关的文章,稍作回顾和评论。这倒不是因为我要对我已经不熟悉的自杀研究界的现状随便置喙,而是想借此机会再作一个反思,以求教于诸位仍然从事自杀研究的朋友们。时至今日,我结束自杀研究已经很多年了,这期间,我对自己当初的想法既有继续深化,也有一些改变和修正。回过头来再检讨自己的研究,参照同道们仍然在艰苦进行的研究,可以在几年之后再作一个新的反思。 近些年来,集中于村治研究的华中学者们对自杀问题做了很多非常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比起我十年前的材料(《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所用的材料最晚是2003年的),自然更加丰富,且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他们的研究以群体的方式进行,不同成员之间既有相互的支持和补充,也有彼此的张力和讨论,在学术上形成一个非常活跃的共同体,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这些学者我大多未曾谋面,但他们这些年来的自杀研究,我拜读了不少,非常感佩。这次刊发的三篇文章,也是他们长期研究的优秀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了自杀研究的深化,对我的理论也有不少对话和批评。他们的观点虽然我并不都同意,但我非常愿意听取他们的批评,也非常希望和他们继续讨论相关的问题。借着对这几篇文章的讨论,我也希望表达自己对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的看法,不仅求教于几位作者,也希望与其他读者有进一步的讨论。 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在2003年前后形成一个热点,无论是以费立鹏教授为首的医学群体、农家女的干预项目,还是我本人的自杀研究,最初的起因都在于中国自杀率过高,而对中国高自杀率的发现,则来自回龙观医院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但近些年来,各项研究都表明,中国自杀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如何理解中国自杀率的升和降,也成为中国自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杨华博士的论文《“结构—价值”变动的错位互构:理解南方农村自杀潮的一个框架》(以下简称“杨文”),采用“结构—价值”的分析框架,从文化、社会、心理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自杀率升降的原因,无论是对理论的运用,还是对现实的观察,都是一项相当精彩的研究。我认为,这是目前所见到的谈自杀率变化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我读后受益良多。 作者集中讨论了自杀率最高的两个人群:年轻妇女和老年人。杨文认为,在90年代,这两个人群的自杀率之所以那么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家庭结构变化之后,价值却没有跟上变化,结构和价值之间的这种错位,是两个群体容易走向自杀的深层原因。作者认为,在传统社会,由于宗族观念强,家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关系,强调等级性,父对子、夫对妻都有比较绝对的支配权,相应的价值目标上,也比较强调宗亲关系、香火观念、尊老爱幼、孝悌忠信、三从四德等等,因而结构和价值是相匹配的,家庭关系是稳定和平静的,也就没有多少自杀的事情发生。但在近三十年中,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祖先崇拜降温,核心家庭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夫妻关系取代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家庭实现了平权,代际关系平等化,男女之间也趋向于平等。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应该是和新的价值观相匹配的。但是,一方面,年轻妇女的价值观念和预期都提高了,要求获得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但她们实际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已经降低了,但观念却没有相应地降低。因而在两方面都出现了变动不一致和不匹配的现象。两个群体的问题都是实际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心理预期高,在现实中受挫之后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感,结果导致家庭矛盾极其紧张,冲突不断。这就是这两个群体自杀率比较高的原因。 杨文的这一判断和我对八九十年代中国自杀状况的理解相当一致(顺便说一下,杨博士认为我持的是静态价值决定论,这是不对的;但这一小错无关大局)。我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反复强调,目前中国自杀率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与家庭结构变动导致的价值和伦理失衡。传统社会的价值和结构都是稳定的,有明确的规则可循,但现代中国在经历了社会革命和家庭革命之后,新的价值体系却一直无法确立起来,这是导致家庭冲突和自杀事件频繁的根本原因。而且我也认为,这并不只是农村社会的状况,也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状况,虽然在城市里表现得没有那么尖锐,因而并不总是直接导致自杀。 既然自杀率升高的原因来自家庭伦理的失衡,那么如何来理解自杀率下降的原因呢?杨文遵循了同一思路,认为在进入21世纪后,当初结构和价值失衡的状况逐渐得到了转变,已经越来越匹配了,这就是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作者看来,在近十年多的时间里,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在家庭中越来越处于与男人平等,甚至还要高一些的地位,家庭冲突不再那么激烈;老人也比较认同他们已经下降了的地位,学会了“做老人”,因而也就能比较心安理得地面对他们所处的状况,不再要求子女那么孝顺他们,所以在出现问题和冲突时,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落差。这样,两个群体的价值观和心理预期都与社会结构状况相匹配,相一致,就不再出现那种因落差很大而导致自杀的状况了。这就是自杀率逐渐下降的原因。 对于自杀率下降的分析,一方面我仍然觉得应该非常认真和严肃地对待杨文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也有些疑虑。而我和目前对自杀率下降的研究者最大的一个分歧是,我并不认为自杀率下降就一定是好事,更不认为自杀率下降就意味着导致自杀的最根本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自杀这一复杂现象,从来都是由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因而世界上的自杀干预项目虽然很多,但哪些确实降低了自杀率,却非常难讲。费立鹏教授在很早的时候就曾谈到这一特点。虽然我们认为,家庭伦理的失衡是农村自杀的深层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杀就是这种失衡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并不能推出来,自杀率的降低一定就是由于那种深层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用怀疑,杨华博士所描述的妇女地位上升和老人价值预期降低,都是确实存在的事实;而且这些也可能和自杀率下降有一定的关系。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家庭伦理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稳定和平衡的状态呢?当读到杨文中所写的“老人学会做老人”的时候,我感到的并不是自杀率降低之后的轻松,而是一种非常无奈的苦涩。这只能意味着,价值的跌落已经到了麻木和虚无的程度,而并不能表明已经形成了新的价值。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更像是个完全没有价值的时代,而非获得新的稳定价值的时代。还是上面所说的,伦理失衡和价值缺失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恐怕还更加严重,因为人们已经不愿意为任何价值而舍去生命了。这些问题不再以自杀的方式表现出来,可能意味着,我们将面临远比自杀严重得多的问题。 我一直非常看重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的一个基本判断:虽然自杀率过高的社会是有问题的,但自杀率过低的社会是更成问题的。我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中也谈过,一个自杀率过高的社会虽然是有严重问题的社会,但一个完全没有自杀发生的社会却是没有出息的社会。杨文似乎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正在一步步变成没有出息的社会。 虽然对杨文的一些结论不能完全赞同,但我仍然非常喜欢这篇论文。作者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呈现出来,虽然本身是在谈问题的解决,却能让我从中看出与作者完全不同的东西,恰恰说明杨博士非常忠实地展现了现实的复杂性,而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极高境界。 陈柏峰和郭俊霞两位博士的文章,与杨华博士的文章紧密配合,可以说是对杨文的结论的具体诠释,是对当代中国家庭政治不同方面的深入研究。前者针对的是未婚青年自杀状况的变化,后者针对的是婚姻家庭状况的变化。两位博士的基本判断也和杨文非常相似。虽然他们的文章并未涉及老年人自杀,但他们的基本观点都可以纳入杨文的“结构—价值”错位的判断当中。 陈柏峰博士的论文《反抗与绝望: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未婚青年自杀》(以下简称“陈文”)集中于农村青年的自杀,认为农村青年的自杀主要有三个类型:第一个是婚恋问题导致的自杀,主要是因为父母干预婚姻引发的;第二个是家庭琐事导致的冲突引发的自杀;第三个是生活中的困境而导致的自杀。陈博士在全国范围内的若干村庄中收集了大量的自杀案例,既对它们作了细致的分类和统计工作,也详细记录了许多典型案例的发生过程。陈文资料翔实,分析清楚,也是一篇非常优秀的研究论文。文中提出的几个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他所谈到的第一类自杀案例,即年轻女子因为婚姻自主权而导致的自杀,我在研究中也遇到过几起,这呼应了现代中国家庭革命的一个主要命题。不过,这类自杀案例在我的研究中发生得比较少,没有陈文中这么频繁。而且,我听到的当地村里人的反应也和陈博士所写的不大一样。就在事情发生的同时,人们也大多指责父母干涉女儿的婚姻,过于顽固和蛮横,而不像陈文所写的那样,指责女儿自杀是不孝。这可能是由于地区差异或其他因素造成的。 陈文认为,虽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在20世纪50年代就颁布了,但在三四十年之后,传统的力量仍然很强大,父母仍然把干涉儿女婚姻当作理所当然的,甚至周围的很多人仍然支持父母的做法,指责这些女儿的自杀。这表明年轻人追求婚姻自由的价值取向与父母相对传统的价值取向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而在进入21世纪后,由于婚姻自主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样的自杀案件越来越少,甚至几乎绝迹。其实,我本人在田野研究中遇到的这些例子,有些就发生在世纪之交,其中一例是2002年发生的。20岁的女儿因为父亲反对自由恋爱而喝农药自杀,周围的人都指责父亲过于顽固。或许正是因为陈博士所说的原因,即这时候人们的普遍观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陈文对于这一类自杀案例的分析相当细致和精彩,几乎无可挑剔,我也完全赞同陈博士关于现代与传统价值观冲突的理论视角。但我还是有一点疑问:是不是所有这类案件都必然是新旧价值冲突导致的,在比较接受现代观念的家庭中是否就一定不会发生因为婚姻自主问题而导致的冲突与自杀呢?我们不妨把角度稍微移向父母,替他们想一下。父母关心儿女的婚姻和终身幸福,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关心后代的幸福而担心他们找的对象不够好,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样的事情上,两代人之间因为观点不一致而发生冲突,女儿明明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一赌气自杀而死,这是否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陈博士说:“青年女孩因为受父母干涉,不能跟自己心爱的男孩一起而选择自杀,其本质是对婚姻自主权的争夺。”这一判断恐怕略显简单了。我承认这样的自杀案件往往可以理解为对婚姻自主权的争夺,却不认为其本质是对婚姻自主权的争夺。即使在婚姻自主观念已经完全确立的今天,父母仍然会关心子女的幸福,只要有这种关心,就有意见不一致的可能;而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只要有人不够理性,就有可能发生冲突甚至自杀,甚至可能像陈博士所说的那样,父母也可能因此而自杀。要说目前这种自杀案例已经绝迹,恐怕还是过于乐观了。而陈文在最后说,外出打工导致的人口流动,摧毁了父母干涉婚姻的结构性因素。这种因素,与婚姻观念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它所带来的,怕是也不只是婚姻自主这样令人乐观的结果吧。 第二类自杀,是因为家庭琐事导致的冲突而自杀,特别是因为干活累而自杀。陈博士举出了七个这一类型的案例,叙述和分析都相当精彩。但他集中于因为干活累而自杀的案例来作分析,是我不大能理解的。我的研究中虽然也发现了因为干活累而自杀的陆离,但这是极少数。认为这种自杀代表了因家庭琐事自杀这一类型,未免有些偏颇;通过分析干活累这种自杀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自杀,恐怕是没有很大说服力的。至于陈文所说的,男女平等、追求幸福的观念使青年厌倦了劳动的论点,更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陈博士说:“他们渴望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摆脱世世代代的生活,他们渴望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不甘于做一个依附者,独立而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混淆。现代追求自主和独立的精神,绝不意味着好逸恶劳,更不意味着逃离家庭。 第三类自杀,是因为绝望的处境而自杀。陈文又举出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大多是因为找不到媳妇而绝望自杀,也有些因为家庭环境恶劣,甚至因惧怕高考而自杀。陈博士认为,这类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会不够多元,这些年轻人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而一旦某一方面失败了,他们就当成自己人生的全面失败,结果导致了自杀的悲剧。他的这一分析,仍然是相当准确和有见地的。 陈博士认为,随着现代性观念的逐渐确立,随着社会变得多元化,整个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健康,因而上述的自杀类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和杨文中提出的问题一样,这究竟是对问题的进一步解决,还是社会的进一步恶化呢?就像他在分析第二类自杀的时候所说的:“他们不但要面对现实中机会匮乏的残酷性,还要面对让他们很难接受的亲密关系。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难以逾越的强大的结构性力量。既然如此,那还不如一死了之。”陈文对这一困境的揭示相当深刻,但它恐怕并非通过社会的多元化和现代化就能解决得了的。 从我个人的品味和研究旨趣来看,郭俊霞博士的论文《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关系与妇女自杀——鄂南崖村调查》(以下简称“郭文”)是这三篇文章里最值得称赏的。无论从对材料的处理、理论的分析,还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敏感上面,这篇文章都堪称上乘之作。或许是因为集中于崖村这一个村子,而不是像另外两篇文章那样作较多横向的比较,郭文深得人类学研究的精髓,读起来引人入胜,使人在活生生的案例中,能深切地体会到崖村生活状态的息息变化。 在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中,在《婚姻法》颁布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妇女地位的提升、家庭结构的改变,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阎云翔教授和我的书里都不同程度谈到了这种变化。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细致变化过程应该如何梳理,我们却都没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而郭文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作者通过对小小崖村的自杀、离婚、性关系等几个方面现象的详细梳理,具体而微地展现了现代中国妇女在婚姻生活中逐渐取得自主地位,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的过程。 50年代《婚姻法》标志着新型婚姻关系的确立,它颁布之后,曾经有过一段妇女离婚的高潮,这是人们已经熟知的事实。但郭文指出,这只是一段时期的暂时现象,过了这一热潮之后,妇女依然依附于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以崖村为例,在《婚姻法》颁布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三起离婚案件,然后就再无离婚案,直到1999年。当然,离婚的增多并不必然标志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因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离婚毕竟意味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但恰恰是在这种惨痛的解体当中,妇女的自主性得到了张扬。为了强调妇女的自主地位而欢呼离婚率的提升,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科学家极为残忍的一面;但妇女地位的提升,又确实是以离婚率为重要指标的。这对矛盾,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于郭文当中。 在崖村,六七十年代的家庭中,男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家中打老婆是常事。改革开放之后,女性进一步退出公共舞台,回归家庭生活。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妇女逐渐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导,女人当家是越来越常见的情况。在此,郭博士揭示出中国女性解放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女性恰恰是通过在家中获得主导地位而取得自主性的,对西方女性主义主张家庭契约化的倾向无疑是有力的批驳。在这个时期,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离婚使男性付出的代价更高,打老婆的现象逐渐消失,男女平等的理想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从改革开放前期到21世纪,家庭和婚姻状况都有非常重要的变化。在八九十年代,夫妻冲突经常发生,家庭暴力非常频繁,妇女经常以“闹离婚”为争取地位的策略,但并不想真正离婚。那个时期,因为家庭暴力、丈夫婚外性关系而导致的妇女自杀非常普遍。郭文列举的11个案例都是这种情况,但真正离婚的一个都没有。1997年的一场逃婚事件,成为崖村婚姻史的一个转折点。崖村的婚姻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之后,家庭暴力很少发生,离婚案件却大大增加。1999年,崖村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起离婚案,也是50年代以来的第四起离婚案。而在此后的13年中,崖村共发生了11起离婚案,其中只有三起是男人主动提出的。这还是附近地区离婚率最低的村庄。离婚案件的骤然增多,意味着崖村生活状况的巨大改变。妇女不再以照顾家庭和儿女为生活的重心,对爱情和体贴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性生活的质量也被公开地当作离婚的理由。 伴随着离婚率的升高,崖村人的性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郭文以大量生动的个案描述了这十多年来性观念的戏剧性变化。在八九十年代,村里人对男人的婚外性行为一般比较宽容,对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却非常苛刻,妇女会因为丈夫的婚外性行为和他争吵,但往往不会因此而离婚;而女性一旦发生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几乎是必然的,由此导致女性自杀的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但到了21世纪,村内的婚外性行为大量减少,而外出嫖妓的事情则越来越多,男性对女性的婚外性关系也越来越不苛责,女性对于丈夫不加感情色彩的婚外性行为也比较宽容。未婚女性发生婚前性关系,不再使她在婚姻市场上跌价,已婚妇女发生婚外性关系,丈夫也不会对她施加暴力或过于苛责,甚至会求她不要离婚;不少当过“小姐”的女性,也堂而皇之地进入婚姻生活,不再因为她们的经历而遭到歧视;甚至还有女性一直保持着“二奶”的身份。于是郭博士指出:“这些一方面反映了男女日趋平等,另一方面反映了感情在婚姻关系中确实越来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因婚外性关系而导致的妇女自杀,既不可能发生,也难以理解。” 无论是离婚率的增加,还是人们性观念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自杀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自杀率。郭文所勾勒的这一过程,确实呈现出中国妇女争取平等和自主地位的艰辛路程,表明了现代中国家庭革命的成果在一步步深化,传统社会对妇女的禁锢在一步步被打破,男女平等已经逐渐变成了社会现实。不过,郭文结尾也非常尖锐地指出: 然而,对个人现世幸福的追求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一不小心可能迷失了自己,伤着了别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农民在个人现世的幸福中寻找生活的价值时,他们真的可以找到吗?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里,什么才是他们的生活价值?他们如何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价值?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虽然只是到了文章结束的时候,问题的复杂性才被真正明确地提出来,但无论在前文的叙述当中,还是在作者的分析当中,读者都能体会到这把双刃剑的威力。离婚率既是妇女独立自主的重要指标,也是人生和家庭的一大惨剧;妇女已经不再因为顾忌孩子而不肯离婚,这纵然体现了她们对情感的执着追求,但此举给单亲孩童带来的生活和心理伤害却是极其深刻和决定性的。我所接触的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很少有快乐和健康的。至于性开放这种所谓的“先进理念”,郭博士已经用她的双引号表明了态度。我们看到的是肉体决定精神、淫乐决定幸福的喜新厌旧、丧尽廉耻。 在这三篇文章中,郭文是最深地触及到现实的这种复杂性的一篇。她的文章娓娓道来,不卑不亢,对现实的描述和分析都入木三分。也正是在这样揭示出经验生活的复杂性的文章中,希望才能真正成为希望,无奈或许也会渐渐得到理性的化解。 以上是我读这三篇论文的简要评论。对几位作者的主要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我都是相当赞赏的。以贺雪峰教授为首的华中学人高度重视经验研究,因而时刻关注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的走向有着强烈的敏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外,他们非常强调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试图以中国式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现象,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点。目前,这个群体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材料,做出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而且已经有了相当强烈的理论意识。如果能够在扎实的田野研究的基础之上,博采中西理论之长,相信他们会有更优秀的成果。而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研究特点。 三篇文章补充了很多我没有看到的重要内容,也续写了我在2003年结束调查之后的自杀状况。我非常高兴他们能把中国的自杀研究推进到现在这个程度。因此,在阅读他们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我不曾知道或没有深思过的东西,所以我在他们的研究中学习了很多。而我个人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自杀不是绝对的坏事,自杀率降低也不是必然的好事。我与杨华、陈柏峰两位博士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我觉得他们有些过于乐观了。而对于郭俊霞博士提出的问题,我深切地感到心有戚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虽然承认自杀是透视中国社会现状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点,但它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最根本的症结所在,因而即使自杀率降到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无忧无虑的天堂。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随着自杀率的降低而可以高枕无忧,请读者和三位作者原谅我在过去的研究中曾经犯下的错误,以及现在的评论中可能有的误解与唐突,而一起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问题与可能的走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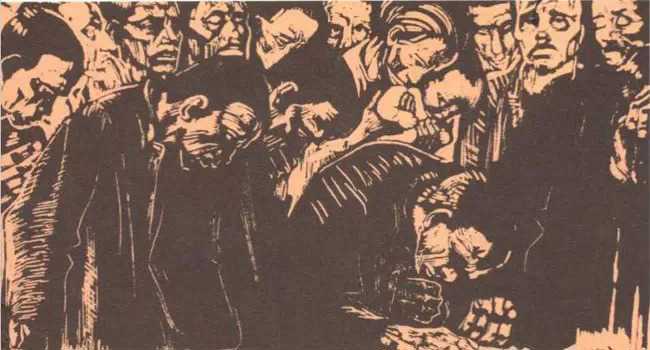
燕南园爱思想 吴飞 2015-08-23 08:48:4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