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阿伦特》: 哲学爱好者必读 一日一书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阿伦特》 [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中华书局/2014-1 北大、人大、复旦、武大等校30名师联名推荐:哲学专业学生、文科大学生及哲学爱好者的必读书。 本书首先简要回顾了阿伦特的生平,帮助读者通过其经历来了解阿伦特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并就其关于极权主义、人类的境况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清晰论述。她的哲学研究清楚地显示了那种在她看来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的前途和希望,并同时为当代的哲学、政治、伦理、社会等启迪着的重要问题。 出世与去世之间 汉娜还在她生命的这一阶段初次体会了政治的重要性。玛尔塔·阿伦特把她的家向社会民主主义者敞开了大门,并且加入了一个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团体。尽管她反对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s)——该同盟系由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但她却是卢森堡本人的崇拜者。在1919年,她支持由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所领导的大罢工。伊丽莎白?扬-布鲁厄尔——汉娜·阿伦特的最为详尽的传记的作者——记述说,玛尔塔让她的女儿记住,她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尽管革命最后失败了,玛尔塔·阿伦特仍然继续她对德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参与。 1920年2月,玛尔塔·阿伦特嫁给了马丁·贝尔瓦尔德(Martin Beerwald),一个带有两个女儿——爱娃(Eva)和克拉拉(Clara)——的鳏夫。玛尔塔和汉娜搬进了贝尔瓦尔德家,两个家庭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然而,汉娜从来没有真正地认同这个整体,她通常更乐于自行其是。她开始吸烟——这一习惯后来伴随她一生,并且创立了一个“希腊学圈”(Greek Circle)的团体。她和朋友们一起在她在贝尔瓦尔德家中的房间里阅读和讨论古希腊经典。她开始钻研克尔恺廓尔(Kierkegaard)和康德(Kant)的着作,并且借写诗来抒发她在情感上的模棱与彷徨。在一首题为《厌倦》(Weariness)的诗中,她写道: 我所爱的 无法把握。 环绕我的 无从摆脱。 黑暗弥漫 万物消隐。 没什么能把我征服—— 此乃生活的真面目。 她的智性成长正在开始,1924至1929年间在大学度过的岁月,为她提供了跟随20世纪最令人激奋的一些学者学习的机会。 求学经历 18岁时,汉娜·阿伦特就读于马堡大学,跟随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以及哲学家尼古莱·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海德格尔当时正处于酝酿他的主要着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的时期。阿伦特参加了他的讲座,并且被海德格尔开辟的激动人心的新的哲学路径深深地影响。尽管她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同海德格尔的分道扬镳,但是她的思想在根本上被她在马堡的这段求学经历所塑造。 当阿伦特到达马堡的时候,海德格尔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并且已经35岁了。他在获得一个大学教席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并且刚刚开始建立起他在哲学界的声誉。阿伦特既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所折服,又被他作为一个成熟男人的风度所吸引。海德格尔冒着失去他的职位和婚姻的危险采取主动,开始了一段风流韵事。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段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遂于1925年将其终止。尽管此后阿伦特又继续保持了数年同海德格尔之间的联系,并且在二战结束后重又恢复了与他的友好关系。在友谊重新恢复时,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她是他许多思想的灵感之源。可是在1925年,他们心照不宣地就这段恋情达成默契,她离开了马堡,首先在弗莱堡,继而在海德堡继续她的学业。 在海德堡,她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espers)。他在她此后的生活中一直是她的导师和朋友。同海德格尔一样,雅斯贝尔斯也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他是从心理学半路出家投身于哲学的,相比海德格尔,他对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更为关注。他对阿伦特智性上的影响显然不如海德格尔,但是他以身作则为她示范了一种生活方式。阿伦特后来意识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以沉思为其特点的。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ove in Augustine)。 在这一时期,她重新加强并深化了同汉斯·约拿斯(Hans Jonas)——她在马堡结识的一位同窗——的友谊。这一友谊——就像同雅斯贝尔斯的一样——持续了她后来的整个一生。她还密切了与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的关系,她在马堡期间就与之相识。他们很快开始同居,并于1929年9月成婚。斯特恩帮她编辑整理了博士论文的定稿,完成后,他们搬往法兰克福,以便斯特恩能够着手获得他的任教资格(Habilitation)的预备工作。在德国的学术体系中,这项工作包括进行任教资格演讲和提交学术论文,这些都是获得一项大学教职任职的初始程序。 在法兰克福的经历以及迁往柏林 斯特恩正致力于一项音乐哲学方面的课题,由于法兰克福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集聚地日益增长的声望,他希望能够到那里任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当时也在法兰克福,斯特恩和阿伦特都参加了他的讲座。就在同一时期,一群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就是后来着名的法兰克福学派(TheFrankfurt School)的前身。尽管斯特恩和阿伦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还是同这些思想家进行了哲学上的交流,阿伦特开始对政治问题越来越感兴趣。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赛(Herbert Marcuse)和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当斯特恩递交他关于音乐哲学的论文时,阿多诺作为同一领域的研究者和论文的最初读者,枪毙了它。 其间,纳粹的势力正在日益增长,斯特恩意识到了大学中的反犹太主义思潮,加之他的论文被驳回,使他获得一个教职在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他和阿伦特决定迁往柏林。在那里,斯特恩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并化用了一个笔名——君特·安德斯,他在后来的整个写作生涯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在柏林,阿伦特开始写作一部拉赫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传记,并且恢复了同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的交往。布鲁门菲尔德曾是她祖父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名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这两件事都使得她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她而言,做一名犹太人,特别是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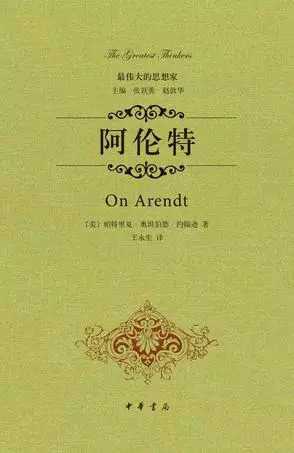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5:4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