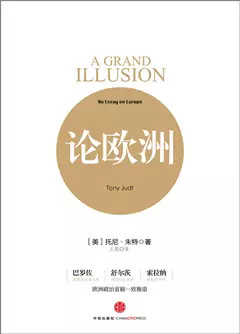|
相關閱讀 |
世界上存在几个欧洲? 荐书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存在几个欧洲?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显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欧洲,正如只有一个亚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样,欧洲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各部分还可以继续细分。诚然,欧洲东部的边界是模糊的,沿着一片广大的、地形学上不明确的地域与西亚接壤;但其他部分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此外,欧洲是一个自我意识历史悠久的小洲,这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根据地理起源决定的“非洲人”“亚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确。比如,尽管人们偶尔会尝试确立某种“泛非洲”意识,但把非洲人联系起来的几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相反,“欧洲性”则是欧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缘关系和共同的过去,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某些天生和基本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在各族群内部和之间划清界限是这个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维定势之一。这个过程始于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单一实体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总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巩固了分裂的结果,让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欧洲西部拥有了明确和稳定的边界。查理曼于9世纪建立的帝国与“二战”后最初的“六国”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覆盖了法国、联邦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意大利,尽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罗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国没有精确的边境线,而是把界墙(limes)、边境区(marches)和军事区作为边界;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界和拜占庭帝国的北部边界一直是不精确的。但到了14世纪,当欧洲的边界“封闭”后,东西欧洲的区别也变得极为明显。
今天,人们有时会认为,东西欧的分割线是冷战时期的人为产物,是在单一文化空间内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铁幕。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乌克兰的广袤土地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说过一句名言,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他不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无论他们的偏见源于何种动机,这两位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提到和证实了一条从北向南贯穿欧洲中部的隐形分割线。15世纪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惊人相似的忿恨之词:“我们着名的但泽港(Danzig)落在波兰人手里,我们的出海口厄勒海峡(Sound)落在丹麦人手里。”在三个多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将成为当代欧洲冲突的导火索。但策尔蒂斯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抱怨说,东部的某些聚居区“被从日耳曼本土分开……比如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萨克森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语。”
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从易北河以东开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样,策尔蒂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描绘的是一种从10世纪末开始便在西欧反复出现的情感: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由于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纪)欧洲唯一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日耳曼定居者向东部的迁徙,西欧人会自然而然地把东欧的土地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蛮人。即使当这些人早已成为东西方帝国的臣民后,上述态度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所有的欧洲帝国都和某种统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别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作为它们继承者的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只有东部的帝国逐渐把世俗和精神权力联系甚至结合起来。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历史悠久的教会区划和习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所有分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国天主教的教区体系借鉴了罗马帝国行省组织的地理划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统治者赋予基督徒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特别是军事效劳)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该地区标签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这种社会—宗教的分歧也体现在语言上。正如说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标识,在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信奉东正教的农民说立陶宛语、罗塞尼亚语或其他土语和方言,而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则说波兰语。到了19世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各地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觉醒,这大多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语言并不古老,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被发明(或改造)的;选择某一种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方言作为未来国家的“民族”语言也许不完全是随机的,但无疑是武断的。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历史上,或者在西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史上,这些分歧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永远比不上东西欧之间的隔阂。这是因为从近代史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
诚然,西欧的经济和文化重心经历过巨大的变迁——从莱茵兰到伦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纳,随后又回到低地国家,最终停留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国的首都。但它们很少会过于偏东,甚至从未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荣,它们从来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就像某个历史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那样。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和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历史的中心大幅转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在白山战役中的失利无疑是波西米亚的一场历史性灾难,因为16世纪的布拉格刚刚经历过学术和艺术的繁荣。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终结了波兰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尽管没有终结它的长期梦想)。上述事件都已成为过去,但从此以后,我们眼中的大部分欧洲史实际上都是西欧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说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西欧具有明确的边界,而不幸的东欧同样如此,那么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是不是从的里亚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泽)的古老连线?既然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地区(某些部分)的界线,以及1947年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体现了惊人的一脉相承,那么是否足以得出结论,它们中必有一条可以作为分界线呢?从达尔马提亚沿岸到立陶宛,的确存在着一条由要塞、边境定居地、战略性村镇和历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组成的连线,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交汇点。但它所通过的地区也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同俄国人交汇、融合和冲突的场所。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远比格但斯克偏东,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镇和山谷仍有人说(或曾经说)德语,而波西米亚则是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当繁荣的地区(没有什么能比工业革命更好地区分西欧和欧洲其他国家了)。为了方便起见,是否应该像许多人提出的那样,单独划分出一个“中欧”呢?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亚斯特到萨格勒布(Zagreb),然后经利沃夫(Lvov)回到波罗的海各点连线为界的四边形区域拥有许多共同点。它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说斯拉夫语的天主教农民,都经历过帝国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建筑遗产和文学传统上,那里的城市和村镇都确定无疑地体现了欧洲主流的风格,同时也带有它们自身的鲜明特色和传统。在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的文化明显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与东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区截然不同,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试图同后者保持距离。因此,该地区的“中欧人”非常看重东西罗马帝国的古老界线,而按照这条界线,他们完全处于西罗马部分。
但“中欧”的问题在于,这完全是一个近代概念,在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晚期的开明专制君主们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打开民族国家独立大门的《凡尔赛条约》几乎已经让它寿终正寝,希特勒只是补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欧”唯一值得怀念的黄金岁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几十年,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经历了前所未有、日后再未重现的繁荣,就连利沃夫和萨格勒布等偏远城市也沐浴在帝国夕阳的光辉下。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欧人)而言,无论在1848年前还是1945年后,中欧和东欧完全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位17世纪的旅行者而言,布达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欧洲中部的缓冲地带与更东面的异域世界的差异。
这种差异当然还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兰东部多沼泽的平原属于东正教的势力范围,虽然语言相近,但用另一种字母表书写,与克拉科夫(Kraków)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是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学术的中心,深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影响,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黑山的高原地区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德语作Laibach)说德语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存在差异的地区都曾是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出现的并非东西差异,而是城乡差异,如果真有所谓“中欧”的话,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希腊,的确存在着一个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赋予布拉格或华沙,布达佩斯或萨格勒布现代意义的那个差异——它们是独立国家的首都——也剥夺了它们加入“中欧”的可能性。它们的文化是都市文化,书面或口头的文化语言是国际性语言——德语,而在说德语的人中,许多最杰出的代表是犹太人。这种真正的中欧文化的毁灭让波兰人的华沙、立陶宛人的维尔纽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达佩斯变成了和奥地利人的维也纳一样的偏远小城。尽管身处欧洲中部,但他们所标榜的独特“中欧传统”最多只是怀旧,甚至可以说是假货。他们不愿被和位于自己东部的土地与民族混为一谈,这种想法是足够真实和根深蒂固的——作为位于欧洲历史十字路口的“边境”民族,他们特别有理由避免让自己在重要的抉择中站在错误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标榜过去或者现在拥有独特身份,以便确保自己永远站在分界线“善的”(和安全的)一边。
更好的做法也许是把欧洲的分界线看成非地理形式的。富欧洲和穷欧洲一直存在,不过两者的分界线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并不固定。在不算太久远的时代,从马赛到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邻内陆城市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贫穷的。但除了少数着名的例外,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更多的是昔日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农村为主的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从汉堡到米兰的欧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荣和发达的中心。
另一组对比的双方是拥有和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差异,但又不仅于此。能在早前的世纪里形成受到认可的民族并建立永久的国家是极其幸运的,这是荷兰、瑞典、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的历史,与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历史的关键性差异之一。北欧和西欧民族的建国过程从核心根据地开始,逐渐吞并周围地区,直到因为地理或竞争限制而停止扩张。而现代东欧国家则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先入者优势,而且它们的身份必然包含对领土和权力孤注一掷的主张,这无疑会损害提出相同主张的邻国的利益——在许多案例中,它们主张的是同一片土地。这是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幸:它们的建国时间太晚,而且凑到了一起。于是,它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和弱点,并因此最终与西欧更幸运的那些民族有了关键性的差异。
《论欧洲》
[美]托尼·朱特(Tony Judt)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
通过明晰、理智和优雅的文字,托尼·朱特将这块曾经分裂的大陆视为一个变化中的整体,梳理了“二战”后欧洲的发展脉络。他认为,西欧战后复兴和重新崛起的有利形势将永远不会重现;而接纳梦想“回归欧洲”的东欧诸国,给不再繁荣的欧洲带来沉重的负担;失业、老龄化、移民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社会问题正在加剧,并到处掀起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浪潮;作为欧洲政治安全阀的社会福利体系压力倍增,面临崩溃的危险……清醒、坦率且极具说服力,托尼·朱特对欧洲历史图景的还原和未来前景的分析发人深省,因而深受欧洲领导人重视。
托尼•朱特(Tony Judt),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2:35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