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动物园(短篇)∣《文学青年》甫跃辉专号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该小说入选2012年度洪治纲花城出版社《中国短篇年选》;2013年8月,入选吴义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短篇卷第一辑;首届人民文学之星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新人奖 虞丽三个星期没来,顾零洲又过上了单身生活。这周末,报复似的睡到了下午四点,饿得受不了了,才起来煮了方便面。吃完后,开始看美国国家地理的纪录片。这曾经是他无上的享受,和虞丽在一起后,竟然没再有过。去他妈的吧,他这么想着,接连看了三集。最后看的一集是《象族》,当大象的身影从摄影机前慢慢远去,解说员说:“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顾零洲无限感慨地回味着这句话,抬起头来,窗外已黄昏。暮色温柔地笼罩了动物园,游人正在散去,一切渐趋静谧。隔着窗,看得最清楚的正是大象的领地。他看得清楚,有十二头亚洲象,厚重的身躯覆满红色的灰尘,矗立在寸草不生的泥地上,像一堵堵沉默的红砖墙。 他蓦然想到,那天,他们竟没去看大象。他原本想,一定要带她去看看大象的,因为站在大象的领地边,正好可以看到他们小小的窗户。 他抓过手机,打了一句话:“这周末可以过来么?”想了想,把“可以”两字删掉,发了出去。他忽然觉得,不会有回音的,她可能从此消失了。这段时间,他一直恍惚觉得,她似乎从未来过。--不过虞丽很快回了消息:“好呀,前段时间太忙了。”他仔细咀嚼着这句话,知道她已经不生气了。他回复道:“上次的事很抱歉,以后--”他不知道是不是该说,他以后想要带她去看看大象。他迟疑着,最终删掉“以后”,把短信发了出去。好一会儿,她只是简单回道:“没事了,下周见。” 顾零洲到地铁站接她,出乎他的意料,她似乎彻底忘了上次的不快,脸上尽是轻俏的笑,“老公”,她低声喊他,旁若无人地在他嘴边啄了一下。虞丽一句没提上次的事儿,顾零洲也不再提。回到屋里,虞丽放下挎包,径直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关上窗户,重又拉好窗帘。回过头来,顾零洲正盯着她。 “看我什么?”她莞尔道。 “没什么。”顾零洲迟了一会儿,嘴角也往上翘了翘。 “老公不想我吗?”虞丽瞟了一眼床,又瞟了一眼他,眼神中满是温软的俏皮。 “想呀,怎么能不想?”他有点干巴巴地说。 抱在一起时,仍旧有一点勉强。顾零洲持续了很久,脑海里不断闪现出那句话:“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这话让他莫名地焦躁。后来,虞丽柔声道:“停下来,好吗?”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不知道怎么,一点感觉没有。”虞丽轻声说。 顾零洲把她抱紧一些,心里莫名地充满了歉疚。 大体上说,他们恢复了过去的生活。顾零洲发现,唯一不同的是:虞丽以近乎执拗的态度坚持关窗。以前,她也会要求关窗,但总是撒着娇征求他的意见:“老公,我们把窗子关上一会儿好不好?”现在,不了。只要一看到窗户开着,她立即会关上。哪怕窗帘拉着,她一闻到空气中那股臭味儿,也会很警惕地拉开窗帘查看窗户关了没有。其实,顾零洲也不喜欢那味儿。但他喜欢开窗,屋子本来就小,老关着门窗就会显得愈发小。在屋里待久了,他会有种窒息的感觉,就如一条被闷在密闭水箱里的鱼。他将什么也做不了,就像那头走来走去的狮子,只能不停地走来走去。 …… 他们默默地恪守着一条原则:不在对方眼皮底下去关窗或开窗。双方的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暗战”。表面上,始终保持着应有的礼节;内底里,其实寸土不让、硝烟弥漫。战争很快由白天蔓延至夜晚。两人躺在床上,总是暗暗较劲儿,看谁先睡着,先睡着就意味着放弃了对窗子的控制权。为了迷惑敌人,两人在伪装上都下了大功夫。顾零洲的伪装方式是打鼾,她知道他很少打鼾,为了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他装作鼻塞。响了两三声后,她小声嘟囔了句什么。他试着调大一点声音。他的嘴巴和她的耳朵挨得很近,他相信,在阒寂的夜里,这可以说是声若惊雷了。她只砸吧了一下嘴。睡得真够香的,他无声地笑了一下,慢慢从她脖子底下抽出手臂,起身推开了窗户。为了保证不发出一点声音,他推得极其小心,推开一点,又回头觑她一眼。月光下,她的脸安静而柔和。花了三四分钟,他才推开了窗户。夜晚的空气清冷、潮湿,什么味儿也闻不到。他眺望着月光下的动物园,大象影影绰绰的,在人们安睡的夜里,它们仍清醒着。这样静谧的时刻,他才真正体会到那句话的含义: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 一早醒来,顾零洲发现窗户关得严丝合缝。 他有点恍惚,难道昨晚自己并没开窗?不对啊,他分明记得自己的一举一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虞丽也像自己一样装睡,或者半夜醒来过。他偷偷观察她,她没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完全是一副无辜的样子。还装得挺像的,顾零洲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他并未由此退缩。除了躺下后努力争取最后睡着,他还想出了一个绝招,就是睡前多喝水。这样,便能保证他半夜醒来上厕所,也就能够保证半夜在检视一遍窗子。渐渐的,他又更进一步,摸索出喝多少水便能在天亮前醒来,这样,可以在白天到来前最后检查一遍窗子。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不管他怎么努力,他早上一觉醒来,窗户总是关着的。他一次次怀疑,睡前开窗加上夜里复查,难道都是梦里发生的事儿?如果不是,那虞丽是怎么做到的?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可怕!她对他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他却对她的所作所为懵懂无知。他看她的眼神,越来越充满了困惑。他总是怔怔地盯着她看,她有太多他所不能了解的了。她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陌生。 就连做爱时,他对她的困惑也未能消解。他盯着她紧阖的眼睛,心想,她多像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呵。或许是太三心二意,整个过程变得冗长、拖沓。汗水密密地布满了他的额头,屋里热得像个蒸笼。鬼使神差的,他微微侧了侧身,伸手探过窗帘将窗子推开了一条缝。猛然间,他感到身子一颠,摔在了床上。虞丽背对窗帘,面无表情地瞪着他。 “顾零洲,你究竟想怎样?” “什么怎么样?我不想怎样啊。”他有点懵。 “没神经病吧你?” 顾零洲瞪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质疑。 “你对我究竟有什么不满?就因为那天在动物园里我生气了吗?你不知道那股尿骚味儿让我多难受!可我一直坚持着,陪着你逛了大半天!我一两周才过来一次,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把窗户关上?你喜欢闻屎尿味,就不能等我离开后闻吗?就算我一周过来一次,那七天里你还可以有五天尽情地闻啊,你怎么就连两天都不能等!你怎么就这么自私!”虞丽拉过被子堆在身上,深深喘了一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下:“你想想,和你在一起这么久,我对你要求过什么?别说房子,就连衣服也没让你给我买过一件!这些我都不在乎,只要我们志趣相投就好。可你呢?我不提要求,你就从没想过要给我什么吗?连关窗这么一件小事都不愿满足我?” 虞丽抽噎着,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滚落。 顾零洲慢慢地红了脸,汗水一层一层地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 “不是这样的”,他支吾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其实那气味没什么……夜里更没什么,什么气味也没有。” 虞丽不解地瞅着他,张了好几次口,才说: “不是我说话难听,你真没毛病吧?你说过的,我是你遇到过的最知心的人,我也曾经认为,你也是我遇到过的最知心的人,我从来没跟谁谈论工作那么投机,可是,现在你越来越让我搞不懂了。你难道还想成为动物学家?想要我跟着也成为动物学家?你喜欢的,不能强制我也喜欢啊。别胡乱找理由了,其实,你不断开窗,只是想让我不舒服,想让我不高兴。很简单,你想折磨我!你知不知道,跟你在一起,我有多少夜没睡觉了?!我以为,只要坚持关窗,总有一天你会醒悟,会心疼我迁就我,可我想错了!” 虞丽湿漉漉的眼睛里却闪烁着仇恨的光芒,有一把火随时要烧到他身上似的。不知道她那瘦瘦的身体里,怎么会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力量。 “不是……不是这样。”顾零洲磕磕巴巴的。被虞丽这么一说,他也开始怀疑自己了--我为什么就那么想开窗? “不管是不是吧,你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谜。我喜欢你,可就是猜不透你。现在,我真的累了,不想猜了。”虞丽眼里仇恨的火焰被不断淌下的泪水熄灭了。 没有虞丽的日子,顾零洲仍旧保持着几周来养成的习惯,临睡时喝下足够天亮前一刻醒来的水,躺下后假寐一会儿,然后检视一遍窗子,天亮前起来上厕所时再检视一遍。不过检视的内容有所不同,现在,他是为了确认窗子关好没有。自从虞丽离开后,他一直关着窗子。他想试验一下,自己能否为了虞丽做一次彻底的改变。 顾零洲深感生活陷入了一团迷雾中,他既想看清去路,也在竭力回想来路。高考让他误打误撞地来到这座城市,毕业后到了现在的出版社,同时到了现在住的地方。快毕业那段时光,他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担忧自己无法适应学校外的世界--工作和生活,都让他紧张。然而,时间一天天催逼着他去面对。他在同学的介绍下找到了现在的住所,房东向他推介房子,说他可以天天免费看动物园了。他至今记得,房东的这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安慰。那时候,他想起了年少时对动物园的印象,想起了自己曾有过的“动物学家”的绰号,以及要做一个“动物学家”的梦想。 回望近三十年的生命,顾零洲惊讶地发现,自己几乎没什么梦想可言。从小到大,他哪方面都不算突出,不会给别人留下什么特别印象。换种安慰的说法,也可以说他哪方面都还可以。进出版社做美编,并非他的梦想,只是他的第一份工作罢了。他适应了,并且喜欢上了--偶尔,他会误以为自己从来就喜欢这个。他几乎没想过换工作。那太危险了,他必定又会如快毕业前夕那样惶惶不可终日。算起来,“动物学家”算是他有过的唯一的梦想了。那么,他现在算是紧挨着梦想生活吧。 是这样吗?这就是我的梦想?好像,又不是。他站在紧闭的窗前,下意识地辨识着夜色中大象们巨大的身躯。他很少计划什么,也很少坚持什么,同样,很少思考什么。他的生活就是顺着一条不需要挣扎的轨迹往前滑动。高考、工作、租房,莫不如是。就连和虞丽在一起,他也有这样的感觉。他想,若非通过网络,他可能不会有勇气对她说那样的话。他本科时有过一个女友,也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话题,即便如此,他也没想过要离开她,直到她大学毕业后离开这座城市。他没和她一起离开,因为他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全新的城市。 现在,他想有所改变了。他不止一次回想起和虞丽生活的情形。他会想象着她的形象自慰,然后心里变得愈加空落落的;会忽然想起一些细节,譬如她的水草一样凉丝丝的头发滑过他胸口的感觉。他回过神来,看到窗外已是暮色沉沉,动物园里的树梢浮着一缕叹息似的橘黄色夕光。他感到茫然的生活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他给她发短信解释说,他之所以那样做,真的只是想让她对动物园破除偏见。他并不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她--再说,动物园也并非他寄寓理想的地方--只是,很想带她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象,因为在大象边,可以看到他们的房子。他知道这是个听起来很难成立的理由,但他不知道除此还能怎么解释。她没表示相信,也没表示不相信。他以为她理解了他。他一次次问她什么时候能过来,她总说最近太忙,过一阵子再说。她曾说过,她住的是老师们的集体宿舍,不方便让他过去。现在,他真想去找她,看看她在自己之外有着怎样的生活。一个多月后,他再发短信让她过来,许久,她回短信说,我们分手吧。 …… 又过了一个星期,虞丽来了。是个晴朗的下午。顾零洲一直设想,两人再见面会是怎样的情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虞丽一进门就脱了外套,往手上呵着气说:“屋外还挺冷的。”已是初春时节,天气似乎并没转暖的迹象。顾零洲笑了笑,“那就别忙着脱衣服啊。”虞丽还是脱下了大红色的长风衣,随手搁在床上。她穿一件嫩黄色毛衣,令顾零洲心头一阵暖热。 “你这屋里味道这么重!”虞丽瞥一眼顾零洲,拧着眉头。 “一个多月没开窗了……可能有点儿”顾零洲红了脸,转身想要推开窗,又停住了。他觉得很尴尬,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合适的。 虞丽似乎也有些尴尬。很明显,她没想到会这样。她慢慢地舒展开了眉头,低了声说:“那我收拾一下吧,你做你的事,别管我。” 顾零洲目光温软的蛛丝一般粘在她身上。看着她收起她留下的拖鞋、内衣、镜子、毛绒熊、化妆品等小东西,同时,像往日一样收拾床铺、擦净桌椅,还拖了地板。为了不妨碍她,他不时挪一下位置,像一件多余的破旧家具,不知道该往哪儿摆放。她注意到他一直盯着自己,抬起头瞟他一眼,一瞬间,眼睛里闪过一点什么东西,又低下头去。“你做你的事呀,别管我。--我没打搅到你吧?”她异常客气。 她不停地在屋里走动,白皙的脸变得红扑扑的,不时抬起手背擦拭额头。后来,她干脆卷起了毛衣袖子。不过,不管如何仔细,屋子毕竟很小,不到一小时,实在没什么可收拾的了。只是,那浓重的气味还在。 “要不,开一下窗吧?”她迟疑地看着他。 “你……能习惯吗?”他探寻地问道。 “还好吧,”她莞尔道,“透透气总比闷着好。” 他也笑了一下。一个多月没开了,窗子有点儿不大灵活了,他用上两只手才推开。霎那扑来的空气竟让他有点儿难以适应。这就是动物园的气味?他有些疑惑地想。 他们并排站在窗前。他看到她大大呼吸了几口气,带着动物园气味的空气。 “那我走了。”她轻声说。 他感到心头突地跳了一下。他攥紧拳头,又松开,再攥紧。她仍旧和他并排站着,并没有走。他鼓起了很大勇气,把手抬起,搭上她的肩头。他如同机器,扭过她的身子,把手放在她的脸颊上,她的脸颊有着薄薄的初生鸡蛋似的温热。她怔怔地盯着他。他也怔怔地盯着她。她的眼眸深处闪烁着一点亮晶晶的东西,是那么……熟悉。这时,她轻柔而又坚决地推开了他。“别这样,”她轻声说。又扭动了一下肩膀,好摆脱掉他的手。一瞬间,他回过神来,不禁又想,他们简直是陌生人。这感觉像一道魔咒,再次牢牢地箍住了他。 “没什么事的话,我走了。”她开始穿风衣。 “我带你去动物园里看看大象吧?”他忽然说,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在大象身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屋子。我们晚上去,就不会有气味了。” 她瞅着他,惊讶得张大了嘴。 “你让我说什么好……对你,我当真是无语了。”她果断地挎了包,“你那么想去,跟你以后的女朋友去吧。” 虞丽坚持不让他送,独自拎着包走了。他趴在另一边窗口,望着她走出自己这幢楼,一径走出小区,始终没有回头。不到五分钟,她的大红的长风衣如一束火焰熄灭在路的拐角处。他呆呆地趴在窗口,凝望着拐角那儿。那一束火焰似乎还燃烧在他的眼睛深处。即便闭上眼,仍能感觉到它在眼帘上熊熊燃烧。再睁开眼睛,他才确认,她消失了。他突然拔腿往下跑,一心想要追上她。他想,他应该和往日那样送她到地铁站的。他追出了小区,追到了动物园门口,放眼望去,地铁站前这一段路上已经没她的踪影了。初春的明晃晃的,使得柏油马路蜿蜒成一条波动的河流。他没再追下去,气喘吁吁地坐在动物园前的马路牙子上,不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 不知坐了多久,暮色在马路上涂下他孤零零的影子。马路上尽是下班回家的人。他木然地站起,两眼茫然,不知是不是也该回家去。一转头看到了动物园的大门,不断有人往出走,快要闭园了,再有几分钟就不让进了。他毫不犹豫地朝大门走去。 他拐过曲折的路径,径直往大象区走。对这家动物园,他实在太熟悉了。可不知怎么,走了半天他才发现迷路了。他又回到了猴子们的假山旁。猴子们嬉皮笑脸地笑话他。他不理会它们,疑惑地望着来路,皱着眉,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好一阵子,他才发现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朝大象区走去。暮色越来越重,树影越来越重。他仿佛走在无尽的时光中。看到大象的那一瞬间,他终于难以自已,感到泪水一再涌满眼眶。透过泪水,他看到了夕阳下正咀嚼着干稻草的大象们。此时,他莫名地觉得,它们不再是庄严和温柔的,它们赭红色的庞大身躯里,似乎隐藏着同样庞大的痛苦。 避过清园保安的视线,比想象中得要简单;在夜色的迷障和十来栋楼的迷宫里辨识自己的窗口,却比想象中难多了。他背靠大象们的围栏坐着,盯着一处黑洞洞的窗口,却总不能完全确定那就是自己的窗口。大象们在不远的黑暗中,它们在睡觉么?大象的睡眠时间很短,只有短短几分钟。如果它们做梦的话,可能都来不及回到家乡吧?这么想着,他想回去了。这儿并没想象中的特别,再说,初春时节的夜还是挺冷的。他出门时只没穿外套,瑟缩着,又望了一眼黑暗中大象们小山丘似的身躯,觉得自己就如一只受伤的动物,要回到自己的窝里去了。一路上,他觉得自己心里是那么柔软,那么孤独,又那么平静。走到大门边,他才发现棘手的问题:动物园的大门黑沉沉地关着。 2010年12月6日6:30:41师大一村 本作品由甫跃辉授权《文学青年》发表,转来请注明出处动物园(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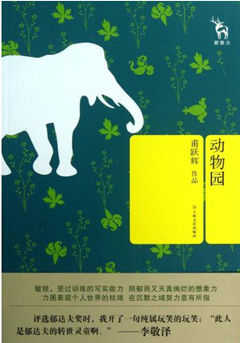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3:02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