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流沙河 锯齿啮痕录 自传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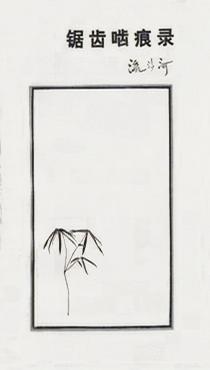
自传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 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 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 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 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 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 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 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 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 (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 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 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 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 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 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 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 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 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 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 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 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 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 ——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 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 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 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 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 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 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 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 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 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 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 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 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 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 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 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 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 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 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 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 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 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 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 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 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 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 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 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 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 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 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汛急往,得一本萧三着《毛泽东 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 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 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 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 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 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 《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 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 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 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 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 《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 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 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 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 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 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 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 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 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 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 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 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 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 “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 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 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 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 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 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 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 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 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 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 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 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 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 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 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 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 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 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 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 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 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 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 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 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 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 “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 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 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 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 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 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 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 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 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 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 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 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 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 《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 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 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 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 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 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 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 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 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 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 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 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 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 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 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 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 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 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 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 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 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 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 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 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 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 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 《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 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 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 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 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 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 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 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 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 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 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 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 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 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 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
流沙河 2013-08-22 13:10:38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