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每日荐书 《双典批判》:《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的文学作品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今日推荐:《双典批判》 作者:刘再复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1年12月 今日主持:吴亚顺 推荐理由: 在学生时代,暑假看电视,总是几部经典剧在银幕上来回翻腾,《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新白娘子传奇》等。有一回和朋友争执起来,因为他喜爱《三国演义》,而我喜欢《西游记》。所谓争执,不过是我一遍遍强调自己的喜爱,至于缘由,并不能清楚说明。 直到阅读刘再复先生这本《双典批判》,一些模糊的看法得以显影成形。刘再复批判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认为这两部作品是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其“流毒”已内化至国人的潜意识里。他认为,双典最大的问题,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具体来说,他批判的矛头指向“造反有理”、“欲望有罪”、“义”与美的变质等。 需要说明的是,刘再复先生1980年代末去国远游,远距离审视中国文化,其中一条路径是批判国民性,《双典批判》即是具体行动。五四以来,批判国民性者多矣,从名着的角度,对社会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说法、口号、命题、社会现象等展开深刻而系统的批判,希求脱离非人性的地狱者,我以为,刘再复一人而已。 精彩书摘: 关于“造反有理”的四点思索 (1)以往谈论“逼上梁山”的现象时,只谈论“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一面,忽略还有另一面是“民逼官反”。倘若我们扬弃历代统治集团把造反者诬称为“匪”,而把梁山的原始核心视为社会底层的豪杰,那么,这些武装了的“民”逼“官”反(姑且也把卢俊义视为官层的一员)与官逼民反一样浸透着血腥味,一样残酷。高俅等迫害林冲,用的是国家机器(替天子行道)与国家名义下的各种卑鄙手段,而宋江等逼迫朱仝、安道全、秦明、卢俊义,用的是“革命”(替天行道)和革命名义下的各种残酷手段。手段不同,却同样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利与灵魂权利,都置他人于极端的痛苦之中与灾难之中。其实,民是人,官也是人,虽然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有差别,但人格是平等的。官僚们仗势欺人,不把老百姓当人,这是黑暗的上对下的压迫;而民间造反集团对压迫的反抗也不可滥杀官员,也不可用人类公认的诸如“杀人放火”等罪恶行为强加在他们身上,对他们强行“改造”。穿着秦明的盔衣战甲去滥杀百姓而让秦明与他的家小承担灾难,又让秦明认同阴谋者的道路,包含着多种心灵摧残、人性摧残。这种民逼官反的形态其实也是一种压迫形态。 (2)确认“造反”的某种历史合理性,同情造反者对“专制制度”或“专制权力”的反抗,并不意味着对反抗者“专制人格”的认同。宋江、吴用、李逵、张顺等强制他人入伙的行为所表现的人格,乃是一种极端专制人格。不尊重他人生命的自由选择,包括政治立场的自由选择,对人实行强制性“改造”和逼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念、立场与道路,这就是专制人格。中国的男子多数都具有专制人格。专制人格用于家庭,便是家庭专制;用于社会,便是政治权力专制。中国虽然发生过无数次反叛专制制度与专制政权的农民革命,但结果只是改朝换代,并未建立新的非专制的政治模式与文化模式,其原因就在于原专制政权的主体与反抗专制政权的主体,其文化心理结构是相同的,都是专制性质、霸道性质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换句话说,皇帝与反皇帝的造反者,官僚与反官僚的造反者,在潜意识层面上是两兄弟,他们只是专制国民性钱币的两面。 (3)中国人,无论是民、官还是知识分子,其生存环境均极为恶劣,而最恶劣之处是在两极性的政治营垒中没有自由选择的第三空间。要么是黑,要么是白,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动。两个阵营的搏斗你死我活,一个要吃掉一个。两个阵营都要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与知识分子依附一方和投入一方,不承认黑白之间的广阔灰色地带。金庸《笑傲江湖》的主人公令狐冲的处境其实是中国人与中国精英的典型处境,他想在正邪两方中独立独行,但不被允许。他既是所谓正教(华山派)岳不群的弟子,喜欢岳不群的女儿,又爱邪教教主的女儿任盈盈。他武艺特别高强,两派都要利用他,利用不了又要加害他。幸而那时的世俗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山林社会可逃避,他最后与任盈盈只好逃到那个不见人间烟火的地方吹奏“笑傲江湖”的千古绝唱。从宋江梁山起义的年代直到现代,中国始终没有第三空间。没有卢俊义存活的第三空间。美国总统下台后,可以不参与政事,写自己的传记,其实他们就生活在第三空间之中,他们所以有逍遥的权利,是因为有一个政治势力不可踏入不可侵犯的个人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如果消失,自由就会丧失。 (4)在《水浒传》展示的从“官逼民反”到“民逼官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两种怪物。一种是专制皇权政治造成的以“高俅”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这种怪物本没有才能、品格、智慧,只有拍马、巴结、献媚的本事,但他仰仗专制机器逆向淘汰的黑暗机能,爬上权力宝座的塔尖并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而造成革命的合理性。另一种怪物,是造反大战车造成的以李逵、武松、张顺的名字为符号的怪物。这些怪物本来质地单纯,但在“替天行道”的造反合力下,一味只知服从杀人的命令,只有力量,没有头脑;只有兽的勇猛,没有人的不忍之心;政治性造反是推翻旧政权的你死我活的最惨烈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战争极为残暴也极为险恶,造反者为了生存与发展下去,无法使用正规手段,它注定要破坏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规则,因此就走向滥杀的血腥道路。而造反集团也需要这种怪物作为他们的先锋,在黑暗中为集团杀出一条血路。于是,这种怪物的产生就成为一种必然。不仅中国的大造反运动如此,其他国家的大革命也如此。关于这种现象,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名着《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首先揭示了这一点。他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许多人把大革命看作是魔鬼在世间显灵。自1797年起,德·梅斯特尔先生便说道:“法国革命具有恶魔的特点。”反之,另一些人却在大革命身上发现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但要更新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使整个世界焕然一新,或者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新世界。在当时的许多作家身上,都有这种带宗教特点的恐惧心理,好比萨尔维当初看到蛮族一样。伯克继续阐述他的思想,惊呼道:“法兰西岂只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所有政府,与其说法兰西一定将成为人类的灾难和恐怖,倒不如说它差不多成了屈辱及怜悯的对象。然而,自这座被谋杀的君主专制的坟墓中,却窜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越人类一切想象力的令人可怖的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惧危险,不因悔恨退步;它对一切固有的准则,和一切常规的手段不以为然,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它便把谁击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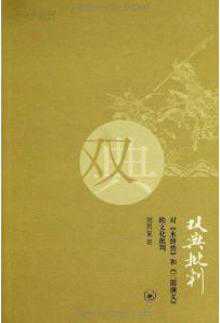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39:5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