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浪漫的理想主义,今何在?
 |
>>> 春秋茶館 - 古典韻味,時事評論,每天清新的思考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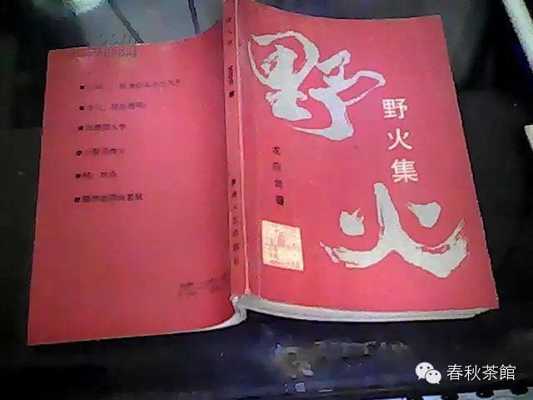
网上“维基百科”是个惊人的创举: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个罕见的“大说谎家”,篡夺解释、颠覆是非,可是总有人起而反对。《洛杉矶时报》够大胆,将自己的社论拿出来,欢迎读者用“维基加注”的方式,对社论进行改写。(这个创意提出两天之后,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险。)
“野火”二十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二十岁的人,今年四十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经和几个人偶遇:那深入部落为原住民孩子争取权益的,那回到乌丘孤岛去为穷乡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组织了环保运动的……台湾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坚持和努力中累积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败了?被什么打败?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今天二十岁的人,当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们所努力、所祈求的环境中长大了,今天和我们站在一样的高度上,眼睛与我们平视。我好奇,当年的“幼稚园大学”,现在是什么?当年的大学生,在威权政体长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的大学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呢? 或者说,二十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倒是我自己,在写过“野火”二十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摊开来请今天的大学生来“维基加注”,你会怎么加呢?
今天的新瓶装昨天的馊酒
譬如说,我承认民主让我困惑。(是否观察过、比较过,印度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比起来,如何?我们是更糟呢,还是不错?)
民主以后,台北每年有跨年晚会,市政府广场和“总统府”广场,在一条街的两头,同时举行。但是“总统府”和“市政府”分属不同政党主政,所以是一个较劲的局面。通常“总统府”钱多,场面也比较豪华。两边请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响乐团或民族音乐或地方戏曲,因为,主政者锁定吸引的“顾客”,是年轻人。
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救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样,溶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地就赢得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摇晃手里的金光闪闪,在青春洋溢的歌声里,露出热切而幸福的表情。当他们情绪里的快乐和感恩激素涨到最高度时,政治人物上场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侠”,他穿着和年轻人一样轻松而“酷”的服装,讲着和年轻人一样俏皮的语言,做出年轻人熟悉做的手势。当他凑近麦克风大声说:“好不好-”广场上的群众,一如他所期待的,响雷一样地欢呼回应,“好-”(你在场吗?)
不管是灯节、圣诞节,不管是挂着什么名目的文艺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乡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歌舞升平、欢乐光明,而在舞台和灯光的后面,基本上是这样的操作:该不该有艺文活动,不是看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选民的好感、信赖和忠诚。于是从预算的编列到预算的使用,从晚会的时机地点到宣传的文字调性,从图腾的挑选到节目的设计,丝丝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销这个政治人物,累积选票。在太多的场合里,所谓文化,所谓艺术,其实包裹在选举的规划里,花的是公家的钱。
讲得更白一点,如果专业告诉你,最迫切需要预算的是山区小学建立图书馆,或者中学艺术教育的深化,但是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资、长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会去做的;一场一场声光绚烂的晚会,一砸几千万,却可以为他塑造形象,赢得选票。钱,就往那个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懒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乐消费者。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反而,威权的统治者因为不需要选票考虑,他可能做长程投资和规划,即使不讨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轮的选举的执政者,却往往选择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换取眼前的权宜。而每一任执政者都以最短距离的眼前的利益为利益,社会发展永远像夜市里的流动摊贩、洼地里的违章建筑,急就章,而且品质拙劣。
(你是否思考过这种矛盾?就是说,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们所创出来的民主,是第几流的品质?没有人愿意往回走的,可是,这往前走的路你看见吗?)
在威权时代,所有的媒体都被统治者垄断,报纸上从头版到尾巴都是领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为。今天民主了,是的,声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论激烈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传?
原来,从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体配合报道,政令宣传都以新闻的面貌出现。现在靠的是市场:媒体需要赚钱,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于是政令宣传再度以新闻的面貌出现。这就叫“置入性行销”。民主是竞争的,但是谁执政,谁就花得起钱,购买媒体,购买知名度,购买政治资本。在野的反对者没这个优势,是活该。而在野反对者一旦得权,马上占尽资源。累积政治资本的钱,全是纳税公民的,而媒体,与他共谋。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还不提财团与政权之间,绵密的暧昧互利。
这些都没错,因为在民主结构里,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大学生、财团,都有自由的公民权利。可是,问题是,今天的新瓶装了昨天的馊酒,那么谁是新时代的反对者呢?
从威权到民主,不是从奴役到自由吗?或者认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不要告诉我,你八岁就知道了这个道理。)

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
着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在十岁那一年就跟着父母住进了集中营,在死亡的阴影、恐怖的环境里成长。解放的那一天,监狱的栅栏被拆除,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现,对劫后幸存的他,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间,他看见一个德国平民被枪杀,看见一个囚犯扑向一包地上的香烟而被坦克车碾过。被幸福感所充满,他告诉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么理解“自由”呢?没有经过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认为自己自由吗?你怎么理解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这个问题和你的个人生活有没有关连?抽象观念和你的具体生命,有没有关连?)
一九四五年,纳粹崩溃,苏联“解放”了捷克,他以为是自由的来临,自由却再度变成奴役,捷克陷入苏联的集权控制。一九九〇年,苏联崩溃,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讲秃鹰如何依靠动物的尸体让自己强壮。自由之于权力,是否犹如尸体之于秃鹰呢?(可以吗?可以这样比喻吗?)
但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腐蚀自由的“秃鹰”有一种流动的面貌,不容易辨认它的轮廓。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逼问克里玛,言词锋利:
……我要说的话也许会给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对自由的穷人告诫致富的危险。你为了某个东西奋斗了许多年,某个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一样的东西,而我要说的是,你为之奋斗的空气也有一点败坏了……随着捷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消费世界,你们作家会发现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敌手所困扰,说来也奇怪,令人压抑的、毫无生气的集权主义曾保护过你们免受这些敌手的伤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将是这样一个敌手,它是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首要敌人……这个敌手实际上使整个人类的语言都变得愚昧。我谈的是商业广告电视,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浅薄的-不是由于一个愚蠢的国家检察官所控制……而是由于其娱乐性几乎所有人都爱看的大量陈腐乏味的电视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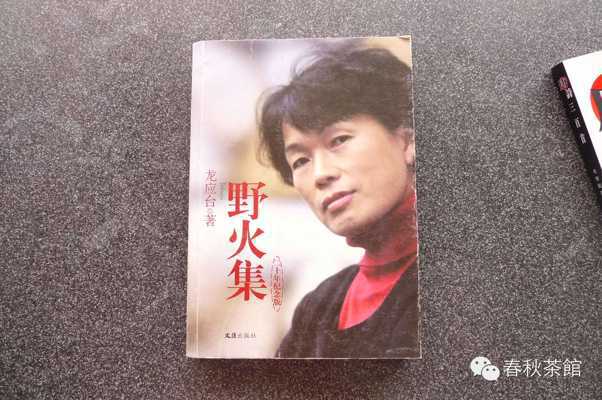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们好容易才冲破集权主义的知识囚笼。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失去什么,还是你们已经知道?
(你在台湾的现实里是否看得见那“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敌人”?或者,你能为这个“敌人”辩护?你拿罗斯的问题怎么办?)
读到这里,我把书阖上,暂且不看克里玛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倒是先自问:二十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变成没有灵魂而机关算尽的豪赌客,政治可能变成纯粹的商品推销术,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转为权力斗争技巧学,知识分子,可能争相以虚无为高尚,而群众,可能比从前更不宽容。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由虚假和童式的愚蠢统治?写“野火”时,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学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园大学”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气壮地嘲笑深刻、拒绝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会把罗素、尼采的书夹在腋下走路,假装“深刻”。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假装”什么?人们又是否夸大了新一代的“虚无”和“草莓”倾向?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所谓“后现代”和所谓“现代”的语意错综吗?)
我得诚实地说,不,我没有料到。事实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用卡夫卡来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记,我写的是:“飞机撞世贸大楼爆炸起火,大楼崩塌像电脑游戏。”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个彻底的私我个人,不是社会人或行动公民。国家层次的惊涛骇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几百万人、千万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懒闲情,等量齐观。有谁比他更自我、更虚无吗?
可是他写出了《审判》、《在流放地》这样的书。这些书里头人性的异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着鲜血的预言,预言十五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人类的大劫难。
克里玛用卡夫卡来回答罗斯的挑战:
(卡夫卡的)这些作品只证明了一个创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实地表现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同时又触及超越个人的或社会的领域……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这是我本人从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把游泳和战争“齐物论”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虚无,事实上,他的“深刻和真实”使得他的个人小我经验可以涵盖甚至于超越国家的大我经验。也就是说,从国家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获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抽空、价值的犬儒化、叙述的琐屑化、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传统的失忆化(这些都是欧化的句子、坏的中文,但是你告诉我是否有更精准的表达句型)。从“大叙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深刻和真实”,不可以离开某些最简单、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则,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与恶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学。(连这一点,你也想挑战吗?)
克里玛其实无法回答罗斯问题中所呈现的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他不无骄傲地告诉罗斯,请放心,在他的国家里,“文学总是不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个不足一千两百万居民的国家,好作家的书,捷克语或翻译作品,都有成千上万的发行量。”
如果罗斯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我会不会和克里玛一样对自己的社会、自己的青年那样有信心呢?说我们的作者和知识精英有足够的“深刻与真实”,能够辨别自由与虚无的分界;说我们的读者和年轻人有足够的品位,探查得出那乘虚而入的“绝对娱乐世界”的全盘统治,辨认得出“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抵挡得住理想主义的消费商品化,鉴别得出价值的真伪?
我想我会沉吟许久。
(好,你怎么回答罗斯?)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词,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同时因为没有了威权政治,没有了压迫,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当然就没有了点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相信“草莓族”这个说法-每个时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对于所谓“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更觉得不可思议。压迫我们的,岂止一个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这些其他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入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叫嚣,进入民主操作中多数的暴力,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所谓压迫,哪里只有一种面孔呢?对于自由精神的压迫,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以不同形式发作,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

龙应台 2015-05-14 21:37:2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