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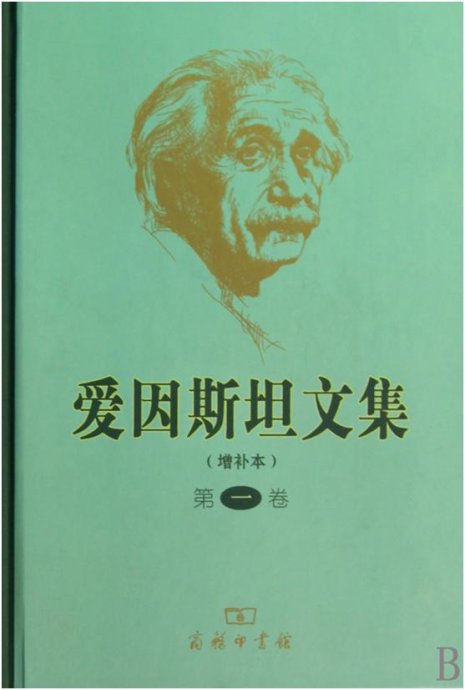
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
我大学时学物理,初中二年级就崇拜爱因斯坦,1938年考大学前认真读过他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使我开始思考人生道路问题。两年后决心投身革命,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和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关”和《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调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斗争,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党籍和公职,回老家当农民,用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母亲。
1962年哲学所所以要组织编译科学哲学着作,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随后展开公开论战。中国领导人企图取代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心。为此,必须批判全世界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各国着名自然科学家的有关思想自然是重点批判对象。因此,必须把这些科学家的哲学着作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编译出来,供批判之用。鉴于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就成为当局第一个关注的对象。让我编译爱因斯坦着作,对我是个喜出望外的大幸事,立即全力以赴。
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他们把我1956-57年译成留在北京的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工分,换取口粮。随后我去北京住了4个月,查阅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全部论着,拟定了选题计划,并于1963年3月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正式约稿合同。
1963年5月,我回家乡,带回由商务印书馆帮助借出的十几种爱因斯坦着作和十来种有份量的爱因斯坦传记。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1960年刚出版的由爱因斯坦遗嘱执行人那坦(Otto Nathan)和诺尔登(H. Norden)编的文献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它全面地搜集了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政治言论。回家乡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批珍贵的文献。
我首先狼吞虎咽地读完了700多页的《爱因斯坦论和平》,对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发现他终生信奉社会主义,虽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向往计划经济,对马克思、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有好感。因此,在政治上,他应该是我们的团结对象,不应该当作敌人来批判。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着作,介绍他的思想了。我日夜埋头于书稿之间,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每夜点着油灯工作到0: 30以后,没有休息日,连春节也顾不上。
在北京期间,偶尔获悉上海科委秘书李宝恒也曾计划编译爱因斯坦着作,于是写信约他合作,他欣然同意。但他工作忙,又未受过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只分担了小部分翻译工作。
经过历时一年半的紧张工作,到1964年10月完成了原定计划,选译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着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气势越来越猛,出版进程受阻。利用这段空隙,我写了一篇9万字的《编译后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17万字的专着《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稿。
为了试探外界反应,我把《后记》和《世界观》两稿中论述哲学思想部分的要点,写成一篇25,000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改(在头尾加上当时流行的套话)后,联名寄给哲学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是我1956年在哲学所创办的),发表于1965年11月出版的第4期上。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不准用真名,只好改用笔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很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写的,党刊不能登右派文章,于是要李宝恒把它压缩改写,用他一人名义发表。
当李宝恒兴冲冲地写出准备送《红旗》发表的文稿时,史无前例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因此成了“阎王殿”(指中宣部)在上海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受到冲击。顷刻间,好运变成了厄运!
二
“文革”一开始,我恢复了全天劳动。随后经历了长期的审查、监禁、批斗,以至死亡的折磨。在生死风暴过去两个月后,又意外地感受到另一场风暴,这就是北京和上海掀起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陈庆振带着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到我的家乡,要向我借爱因斯坦着作的全部译稿,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已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定为理论批判的重点,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我告诉他,爱因斯坦着作的译稿全部在上海李宝恒处。他说上海也在组织批判爱因斯坦,两地的资料互相封锁。于是他把我留下的初稿和资料卡片全部借走。他为人正直,说自己原是学化学的,不懂相对论,要在批判中学习相对论。我坦率地告诉他: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1971年10月从报上获悉商务印书馆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并已恢复业务,我即去信询问《爱因斯坦哲学着作选集》的出版问题。答复是:立即寄去成稿,以便决定。于是我向李宝恒索要。他告诉我,《爱选》和《世界观》两部书稿都于1969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强行“借用”(留有沈贤铭具名的借条),他们不愿归还原稿,只允许由他抄一份还给我。我不同意,写信给沈贤铭和“写作组”,要求归还原稿,他们置之不理。以后打听到“写作组”的头头叫朱永嘉,1972年2月28日给他写了一封挂号信,告知我将于3月下旬去北京(当时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答应为解决我的甄别和归队问题出力,主动要我去北京),要求他必须在我路过上海前归还两部书稿,否则将诉诸法律。3月23日,他果然把《爱选》书稿交还李宝恒;但《世界观》稿却推说“下落不明”,显然是因为这部书稿对他们正在进行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十分有用。
1972年3月29日,我把《爱选》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编辑部,一个星期后就得到答复:此稿重要,决定尽速出版;并表示愿意出版未见下落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稿。在北京两个月,甄别、归队全都落空,但发现了不少9年来国外新出版的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献资料。于是继续同李宝恒合作,分头补译新资料,并复核原译稿。所以要复核,是因为原稿被上海涂改得不成样子,必须一一核对原文才可定稿。我们预定10月交稿,商务也早已把它列入1973年出书计划。
可是,来了一个晴天霹雳。9月18日获悉,上海《科技书征订目录》上赫然有《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所介绍的内容和字数同我们的《爱选》稿完全一样,但编译者却是“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为了揭露和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我写了一篇7,000字题为《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的文章,寄给上海市革委会头头徐景贤。10月12日我带了全部《爱选》译稿到上海找朱永嘉交涉。4天后朱永嘉派代表找我谈判。那个代表先向我传达朱永嘉的四点“指示”:(1)承认《言论集》是以我们的译稿为基础的,可加上我的署名;(2)可立即付给我稿费;(3)商务那边的出书问题不要我过问,由他们联系解决;(4)可考虑安排我的工作问题。这分明是企图用名利来引诱我就范,我不为所动,坚持由商务按原计划出书,你们只能出个节本,并要由我负责看改校样。我看他们毫无知错之意,批评他们的行为是强盗行为。谈判不欢而散。第二天他通过李宝恒通知我,朱永嘉认为他们出书与我无关,不要我看校样。
为抗议上海写作组的强盗行径,我写信向周恩来总理申诉。申诉信请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和秦力生副秘书长转。他们征求吴有训副院长(物理学家)意见后,转给国务院。这封由科学院出面转交的申诉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年3月,他们派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负责人到北京找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丁树奇、陈原协商,达成协议,并上报国家出版局。协议规定:上海的书改为内部发行,商务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不受上海影响。
上海的抄稿经过改装,拖了一年才于1973年10月出版,书名改为《爱因斯坦论着选编》,原来的“编译组”不见了,但在《编译说明》中列了复旦大学12位教师(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集体编译”的,并说“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年至1965年间的旧译稿。”可是,全书有94%的内容是从我们的译稿中抄去的,而原稿尚未发表,竟被称为“旧稿”;强取豪夺被冠以“参考”美名,还要盗用十来位无辜教授的声誉,来压倒我这个没有公职的“摘帽右派”,用心何其良苦。
三
我到北京后,商务把我新拟的选题计划打印出来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国家科委一个干部对书名《爱因斯坦选集》大加指责,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现在要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用意何在?于光远建议改名为《爱因斯坦文集》,我也就同意。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6万字)终于在1974年9月交了稿,一个星期后就送去排印。它能及时发排,在当时是一个奇迹。因为1973年秋冬全国刮起了所谓“反右倾回潮风”,1974年春又掀起了更加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切被贴上“封、资、修”标签的东西谁都不敢出版。连早已编辑加工好了的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样的译稿,商务也不敢发排,唯独《爱因斯坦文集》发排了。这要归功于一年前商务与上海订的协议。
这个时期,上海写作组正在通过他们控制的《复旦学报》、《自然辩证法》等刊物公开抛出一系列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付排,正是对这种张牙舞爪的权势的蔑视。
1974年夏秋,“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商务越烧越旺,原来的领导人丁树奇、陈原靠边站,换了两个不学无术的打手。他们敌视我这个右派,于11月下驱逐令,但当面骗我,说让我回老家继续搞《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证按月寄生活费。可是我回故乡后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停发了我的生活费。正当我的生活将陷于绝境时,恩师王淦昌先生得到这一信息,主动来信,说我以后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从四川寄给我30元。王先生从1960年开始参与我国极机密的原子弹、氢弹研制的领导工作,现在居然要包我这个右派学生的生活费,将承担何等的风险!好在几个月后中国政治风向又稍有转变,商务恢复了我的生活费。《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42万字)也于9月交了稿,由范岱年在北京代我处理。
随着政治气流的回旋,1975年10月我又回到北京。这次是赵中立要我来的。他写信告诉我,国务院成立政策研究室,于光远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个室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这是我争取回哲学所工作的好机会。这次来,当地公社(即乡公所)不给出行证明(当时买到北京的火车票都要证明),商务也不予接待,不得不作为“黑户口”住在赵中立家,一住就将近半年。刚到北京时,恢复工作确实有希望。可是,一个月后风云骤变,刮起批“右倾翻案”风和“批邓”风,一切都成为泡影。本来我又得回老家了,因为商务在接受《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稿后,表示第三卷能否出版是个问题,理由是这一卷全是社会政治言论,会引起麻烦。幸亏我到北京后,于光远通过出版局局长石西民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11月商务通知我:同意我继续完成第三卷的编译工作,生活费发到1976年底为止。由于第三卷内容性质,我约请老同学张宣三参加翻译。
1976年3月,商务终于让我回招待所住,在办公室里工作。半个月后,在我每天早晚必经的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因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事件。7月下旬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整整一个月只能露宿街头。人祸天灾到了极点,苦难的民族终将重见生机。
四
拿到样书,我百感交集,而病魔也在步步紧逼。回到招待所后依然咯血不止,第二天半夜一连咯了一茶杯的血。随后我被送到北京结核病医院。奇怪的是,住了两个月院一直没有查到结核病菌,于是医生怀疑我患的是肺癌,许多朋友都以为我活不久了,纷纷赶来探望,我泰然处之。可是最后也没有查出癌变的迹象。事后估计,当初患的可能是急性支气管炎。在结核病院住了将近4个月后回到商务,编辑室主任高崧和陈兆福很照顾我,让我住在办公室里,边工作边休养。
1973年商务与上海方面协商并上报出版局的协议中规定,《爱因斯坦文集》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但1976年1月第一卷付印时,商务当权者却下令改为内部发行,而且规定封面不得用红色,书名不能烫金。理由是,资产阶级不配用神圣的颜色。于是,封面选用素雅的浅绿色。这引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绿色的文集》(作者为新华社记者胡国华,刊于《了望》周刊1984年第37期)。第一卷印了25,000册,1977年1月开始发行。虽然标明“内部发行”,但书店公开陈列,不到半年即告售罄。
1977年7月,商务决定重印《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并改为公开发行,要我写一篇《前言》。我花了5天时间赶出15,000字的初稿,向周培源等科学家征求意见。一位专管政治思想的编辑室副主任认为此稿是“美化资产阶级”,不能用。另一位曾受我尊重和信任的朋友来信说:此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劝我“头脑不要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种“文革”时的标准语言,值得让后人见识)既然阻力重重,我们只好请周培源先生写序。他欣然答应,但要我们代为起草,说只要把原来的《前言》稿压缩成5,000字,并参考他本人1955年发表的悼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我一一照办。
刊有周培源序言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版终于在1978年3月出版了。3月14日,爱因斯坦诞辰99周年,《人民日报》第三版全文发表了这篇序言。当晚,新华社以《中国出版〈爱因斯坦文集〉》为题,用中文和英文向海内外发布消息,介绍了周先生序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崇高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遗憾的是,这条消息中有一严重失实的内容,说《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着名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我感到恶心,立即去信要求更正,严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着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社员。编译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们5个编译者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难的同志,只不过选题计划是我拟订的,工作量也较大而已。
五
如今,为文集作序、传承爱因斯坦衣钵的周培源先生,编译文集最早合作者李宝恒,以及邹国兴、何成钧、李澍泖三位朋友,都已作古,他们留下的珍贵文字是隽永的纪念。
《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1975年9月发排,1977年3月付型,1977年11月出书。第三卷1977年12月发排,1979年10月付型,1980年3月出书。3卷共选译了410篇文章,共135万字。
在此之前,国外出过9种爱因斯坦的文集。其中以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1953年出版的德文版《我的世界观》,1954年出版的《思想和见解》和1960年出版的《爱因斯坦论和平》最有价值。可惜前3种篇幅过于单薄,最多的不过122篇;最后一种又仅限于社会政治言论。1965-1967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爱因斯坦科学着作集》篇幅最大,有4卷,可惜只限于科学着作,不涉及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言论。相比之下,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可以说是当时内容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
我们热切期盼的《爱因斯坦全集》终于在1987年开始出版了。据《全集》编辑部报告,他们已收集到爱因斯坦的文稿约1,000件,书信9,000件。由此估计,迄今尚未发表的文稿将近20%,书信则在90%以上。《全集》最初计划出35卷,后扩大为40卷,到90年代又改为20多卷。由于人们对《全集》期望值高,编辑人员尽心尽力,战战兢兢,主持人已换了4届,迄今为止只出到第10卷,恐怕20年后才能出齐。这是一项世人瞩目的宏伟的历史工程,我们衷心祝愿它顺利进展。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在刚结束“文革”噩梦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振荡,对由胡耀邦所倡导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1977年下半年,在青年工作干部会议上,胡耀邦说自己买到一本好书,叫《爱因斯坦文集》,他通读了,除了有些部分看不懂以外,凡能看懂的,受到启发很大。1978年9月我应邀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右派”改正问题的座谈会。主持会议的同志告诉我,胡耀邦在中组部(他是1977年12月出任中组部部长的)干部会议上曾号召大家学习《爱因斯坦文集》。这充分表明他的思想开放和虚心好学的精神,也可以说明《爱因斯坦文集》的社会影响。80年代中期,报上曾公布大学生最爱读的10种书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名列其中。
到1994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印了4次,第三卷印了3次,市场上早已断档,要求重印的呼声不绝。鉴于《爱因斯坦文集》成稿于30多年前,当时我尚沉溺于对意识形态的迷信之中。1974年虽然开始醒悟,但依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过程中,凡见到有为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论点,总要在《选编说明》或“编译者注”中加以批驳。现在重新审视,深感内疚,因为这是对爱因斯坦的亵渎,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误导,必须予以更正。现在趁这次再版,把我当初所加上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污染一一清除,并在文字上作了适当校订。同时,把第三卷后面两个“补遗”全部拆散,其中80篇文章按时间顺序分别编入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以求体例一致。此外,两个附录也作了必要的修改。这些处理是否得当,是否仍有污染的余迹,恳请批评指正。
2007年10月6日于北京中关村
供稿人:ZS-GJX
许良英 2013-07-10 16:13:03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