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卡夫卡:任何不是文学的东西都令我厌倦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卡夫卡的小说并不是关于宗教,玄学或者道德问题的论文——他们都是文学作品。卡夫卡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或神学家对我们说话,他只是一个作家”,赫尔曼·黑塞在回复一封年轻读者关于卡夫卡问题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没错,卡夫卡,他是书写了现代人的困境,但我们却不必将他封神。 然而对许多卡夫卡评论家来说,欣赏卡夫卡,首先却是把他放在作家这个身份之外。让·斯塔罗宾斯基说,卡夫卡知道如何给予一部文学作品以宗教意义。曼克斯·布罗德说,我们应该把他的一生和作品放在神明类里,而不是文学类里。皮埃尔·克劳索斯基说,他不仅要创造一组作品,而且还要传递一个信息。 但是卡夫卡自己却是这样说的:“我的情形难以忍受,因为它与我唯一的愿望和唯一的使命——文学——相冲突。”“任何不是文学的东西令我厌倦。”“任何与文学不相干的事情,我都讨厌。”“倘若我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潜力,那只能在文学范畴。” 卡夫卡不顾一切地想成为作家。每当他认为他的愿望受到阻拦时,他都会深陷绝望当中。当他被派去负责他父亲的工厂,他觉得他在两个星期里将无法写作的时候,他恨不得了结自己的性命。他《日记》里最长的一段写了他每天如何挣扎,如何不得不上班做事、不得不应付别人以及不得不对付自己,以便能够在他的《日记》里写几个字。或许,最能代表卡夫卡独特性的作品,是他的短篇。而他,则只是个在繁冗生活中挣扎的书写者。 一道圣旨 有这么一个传说:皇帝向你这位单独的可怜的臣仆,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他在弥留之际恰恰向你下了一道圣旨。他让使者跪在床前,悄声向他交代了旨意;皇帝如此重视他的圣旨,以致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一遍。他点了点头,以示所述无误,他当着为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所有碍事的墙壁均已拆除,帝国的巨头们伫立在那摇摇晃晃的、又高又宽的玉墀之上,围成一圈——皇帝当着所有这些人派出了使者。 使者立即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他就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家屋无止无休。如果是空旷的原野,他便会迅步如飞,那么不久你便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的力气白费一场。他仍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 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了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但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 爱的险境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尖是向外的。无论何时,只要我想要接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这姑娘对此没有罪责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或不如说,我知道她是没有的。前面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围着的,而他们的矛尖是向内的,也就是说是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姑娘那里去时,我首先会撞在我的武士们的矛尖上,在这儿就已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将已是浑身鲜血,失去了知觉。 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待在那里吗? 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挠。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们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 衣服 我经常看到有许多配有褶边和饰物的服装,穿在匀称的身材上,显得很是漂亮。然后我想,这样精致的衣服保持了不多久,要起皱纹,要招尘土,不再平整,服饰变的粗糙,而且去不掉。然而并没有人为此发愁,并且也不以此为可笑。每天早上照样穿着同样昂贵的衣服到晚上才脱掉。 然而,我看见过一些姑娘,她们真是漂亮,肌理骨肉都是很美的,皮肤结实,细发丰满,可成天裹在带头罩的衣服里亮相,她们露出的脸总是手掌大,在她们的镜子里反射出来。 有时候,她们从晚会上很晚回来,在镜子里她们的衣服显得破旧、膨胀,几乎不能再穿了,然而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被晚会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室内滂沱 他用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唇,目注前方,一动不动。 “你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的生意不算太好,可也并不槽糕;再说,即使破了产——这仍然是无稽之谈——你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出路,你又年轻又健康,学过经济学,人很能干,需要你操心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母亲。所以我要求你振作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大白天把我叫来,又为什么这个样子坐着?” 接着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这时我坐在窗台上,他坐在屋子中央一把椅子上,他终于开口了:“好吧,我这就都告诉你。你所说的全都没错,可是你想想:从昨天开始雨一直下个不停,大概是从下午五点开始的吧,”他看了看表,“昨天开始下雨,而今天都四点了,还一直在下。这本来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的事。但是平时街上下雨,屋子里不下。这回好像全颠倒了。你看看窗外,看看,下面是干的,对不对?好吧。可这里的水位不断地上涨着。它爱涨就涨吧。这很糟糕,但我能够忍受。只要想开一点,这事还是可以忍受的,我只不过连同我的椅子漂得高一点,整个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所有东西都在漂,只下过我漂得更高一点。可是雨点在我头上的敲打使我无法忍受。这看上去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偏偏这件小事是我无法忍受的,或者不如说,这我也许甚至也能够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仅仅是我的束手无策。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我戴上一顶帽子,我撑开一把雨伞,我把一块木板顶在头上,全都是白费力气,不是这场雨穿透一切,就是在帽子下,雨伞下,木板下又下起了一场新的雨,雨点的敲击力丝毫不减。” 其实,作为一个“有着特别的力量和个性”的艺术家,卡夫卡一生中与绘画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只不过被他文字的光芒所掩盖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卡夫卡本人并没有太珍视这些画作,他随意地将它们送人,甚至扔进废纸篓。1921年底,卡夫卡在给他的朋友、遗作管理者马克斯•布罗德的“遗嘱”中写道:“我留下的所有绘画作品等,都要毁掉。” 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作画。我想看,想把我看到的东西画下来。我试着以一种完全特别的方式限定我所看到的东西。 ——卡夫卡 卡夫卡《栅栏中的男人》 卡夫卡《用手脚走路的人》 卡夫卡《三个奔跑的人》 《日本杂耍艺人》 《女人头和马腿》 《请愿者和高贵的施主》 文字部分摘自《卡夫卡短篇小说经典》(叶廷芳 译)、莫里斯·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图片选自网络;凤凰读书综合。
弗兰茨·卡夫卡(1883.7.3-192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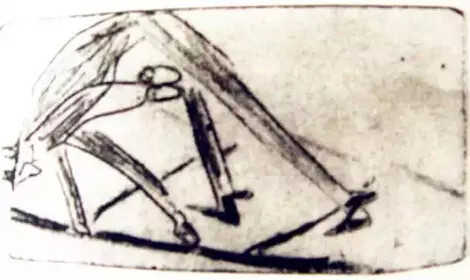


卡夫卡《低头坐着的男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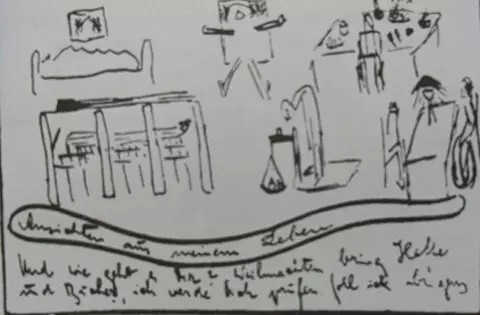
《我的生活》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53:5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